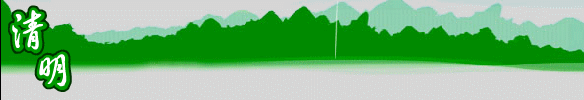阿诗玛—石语谁解?
黄蕙
|
2000年7月21日,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丽坤病逝上海,终年58岁。同一时刻,路南石林,那座似是而非的石像终于圆成了一个神话——“阿诗玛”。
苍蝇公主 杨丽坤是云南普洱磨黑人,彝族,家里十一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九,小名就叫“小九”,也取“长久”之意。小时候,由于她的灵秀,深得父亲宠爱,时时带在身边。父亲好酒,喝酒时也让她抿上一小口,谁知这一口一口,竟练就了她日后的一副好酒量。有人回忆,杨丽坤成名后,逢到国宴、酒会一类的场面,有人让她替酒,小九喝干一杯又一杯,喝罢一巡又一巡,只是不见醉,些许醉意都没有,脸微红而已。宾主无不惊讶感叹。 普洱产茶,有茶就有雾,有雾就有泉,磨黑产盐。茶是苦的,回甜。盐是咸的,回苦。 50年代初,杨丽坤因家庭发生变故,来到昆明与姐姐居住。1954年,进入云南省歌舞团,那年她12岁,脖子上带着红领巾。一张鹅蛋脸,几绺刘海下是泉水一样清亮的大眼晴。一张精致的小嘴,嘴角只要轻轻往上一扬,甜甜的笑就在整张脸上漾开来,仿佛清水上的涟漪。她的个头比同龄的女孩高出许多,这可能是她这么小年纪就被选进歌舞团的原因。十二岁的她,已经出落得如同清水荷花,只等着绽放的那一刻。 小九是真爱跳舞,就像风爱追着云跳舞,泉水爱绕着茶树跳舞,蝴蝶爱围着花朵跳舞。刚到团里时,由于没经过正规训练,她显得有些吃力。第一次登台表演,在一场群舞中,她一时紧张,弄错了节奏,情急之下,居然捂着脸跑到侧幕条后躲起来,观众席里一片哄笑。 第一次登台表演的失败深深刺痛小九。她暗下决心:先把基本功这一课补上。每天早上,她第一个起床,就跑到练功房练“私功”,她扶着把杆,眼睛盯着镜中的自己,正踢腿,200下,侧踢腿,200下,后踢腿,100下……她咬牙切齿,与那一个个数字较劲成仇……终于有一天,她亲眼看着自己咬破层层丝网,蜕化为一只蝴蝶——肢体的柔韧性,这是掌握一切舞蹈语汇必备的条件——她获得了。而她的心灵,那一颗自小与自然万物共舞的心灵,更能在瞬间就准确领悟包含在形体中的内心动作,她的舞蹈更是内心的舞蹈。 只在短短时间内,她就精熟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舞蹈,对于云南之外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的舞蹈,她也一看就会,模仿得出神入画。她痴迷于舞蹈,让肢体与心灵在舞蹈中获得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她在技艺上和舞台上都日益成熟起来,先后在《春江花月夜》、《大青树下》、《椰林怒火》、《南方人民在战斗》等舞蹈中担任主要演员。 有人还清楚地记得《春江花月夜》第一次公演时的情形:幕起,一柱银色的灯光投在舞台中心,女演员长裙曳地,手持两把扇子掩面跪坐在灯光里,裙幅在地上撒开,仿佛水中月亮的倒影。乐起,两把扇子缓缓分开,渐次露出女演员的前额、低垂的双目,好象一轮明月从江面上升起,春花为之含羞,江水为之凝碧……观众席中先是有轻微的骚动,继而是一片啧啧之声。她启开双目的一刹,仿佛皎月轻轻弹离江面,银辉一泻千里……台下掌声雷动…… “杨丽坤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这是她当年的同事对她的评价。这个平时看来在众多如花的女孩中并不是最为出众的小九,只要登上舞台,就会放出太阳月亮一样的光辉,似乎只有舞台,只有观众的才是托举起她的高山大河。或许,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演员,因为舞台上只有美与丑、光明与黑暗,舞台是本质的,舞台又是幼稚的,她是美的、光明的,这就够了。而人生,这个不设观众席,却有隐蔽观众的大舞台,对演员的要求绝没有那简单,它摧毁一切的幼稚,美要在丑中锻造,光明要在黑暗中熔炼。“她总是个孩子。”同样是对她的评价。而她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孩子。 1958年,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为了配合政治宣传,团里排了一出活报舞剧,有苍蝇、蚊子、老鼠和“懒婆娘”四个角色,杨丽坤扮演苍蝇。蚊子、老鼠均有带着尖嘴的头饰,把脸遮去了大半,苍蝇只在头上带了两只大眼晴,整张脸都露着。几场演下来,领导把杨丽坤叫来谈话:“小杨,我们现在演的是‘四害’,你是苍蝇!有那么漂亮的苍蝇吗?有脸那么白的苍蝇吗?观众都光顾着看你了,知道台底下都管你叫什么吗?‘苍蝇公主’!你还笑,还不快去把脸抹抹黑!”听到要把脸抹黑,杨丽坤不笑了:“苍蝇怎么啦!苍蝇也是人演的,人哪有往自己脸上抹黑的,要抹你抹,你当苍蝇,要不你逮只苍蝇替你演。我不演了!”说罢,她把头上的两只大眼睛扯下来,一摔,头也不回地走了。 活报据还在上演,许多慕名来看“苍蝇公主”的人悻悻而归。 那一出“除四害”的剧再也没有人记得,“苍蝇公主”却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蓝靛小衫 1958年,“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省歌舞团派出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到全省各地“采风”。杨丽坤和其他三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被派往呈贡,在马金铺附近的农村,他们发现了一种颇有特色的土风舞蹈——“小龙舞”,舞者两手握住支撑龙首、龙尾的两根木棒,龙身中部在舞者的后颈上固定。舞起来时,长不过两米的“小龙”如同腾云驾雾,有翻江倒海之势,煞是动人心魄。他们如获至宝,潜心学习,决心将它搬上舞台。不久,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筹划的节目已经排定,却没有他们的事。按领导的意思,没有任务的年轻人得去体验生活。于是,杨丽坤和其余三人来到了玉溪东风水库。 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最为壮阔的“群舞”,时代的“配乐”响彻云天,千万人舞步震天憾地。歌舞团来的演员没有什么特别,女孩子加入“穆桂英突击队”,男孩子则加入“老黄忠突击队”,滚一床被子,吃一锅红薯。号角一吹响,“黄忠”、“穆桂英”倾巢出动,推车的推车,挑土的挑土,筛沙的筛沙……笑声、歌声、劳动号子声…… 夜晚,“穆桂英”们已经睡熟,在她们沉稳的呼吸声中,杨丽坤却再也无法平静,她满耳是白天工地上“嘿哟、嘿哟”的劳动号子,满眼是人们穿梭如飞的脚步,她的心随着那号子的节奏跳动:“嘿哟、嘿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旋转、腾越、飞升,如金蛇狂舞——那舞台与梦夜夜叠合…… 一月后,京城舞台,大幕拉开,喧天的锣鼓声中,九条披雷掣电的小龙跃上舞台…… 《小龙舞》在建国十周年晋京汇演中一举夺魁。 似乎杨丽坤还更倾心于她的另一宗收获,离开工地的那天,她竟然舍不得褪下“穆桂英”的“戏装”——那只是一件蓝色土布的左襟短衫,是玉溪地方任何一个劳动妇女最普通的着装。不过,她总算在北城的街子上买到了一截这样的家织土布。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王家乙来到省歌舞团,他要为电影《五朵金花》挑选女主角。“五朵金花”中的前四朵已经敲定,只剩下最后一朵“社长金花”,演员人选迟迟未决。通常,这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探访,那天,是一个礼拜六,按往常的规定,演员们要打扫排练厅的卫生。他走了进去,一群年轻演员正哗哗扫地,其中一个女孩,头上扎一块白毛巾,穿一件蓝靛土布短衫,裤脚还卷起大半截……导演站住了。那女孩确曾抬头相视一笑。导演退后几步,再次站定……他随后转身出来说:“就是她。她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杨丽坤。”——这一瞥,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为中国电影增添了一个光彩的名字。可 多年后,深究其中奥妙的人们还是说,这全赖那件“幸运的蓝布衫”。 这年,杨丽坤才十六岁。银幕上的“社长金花”却是一个成熟干练的妇女干部,这,似乎不可思议——生活与艺术在形象之间不可叠合的“谜”。 1960年,《五朵金花》选送“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杨丽坤荣获“最佳女演员奖”——一个彝族女孩,云冠霞帔,拥着东方红日走到了世界台前。 这年,周恩来总理因国事访问在昆小事休息,那时,《五朵金花》及其女主角已蜚声海内外,并且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在昆明的欢迎宴会上,女宾们盛装出迎,花团锦蔟。周总理一出来就问:“小九呢?小九在哪里?” “我在这儿!”声音从人群的最外一层传来,人们循声望去,很快在她面前让出一条道来。她,依旧是那件蓝靛小衫。脚上,是一双黑布面的搭绊鞋。 风雨圆舞曲 1962年,电影《阿诗玛》的拍摄在筹划之中。当时国家正处在最为艰难的时期。要耗费巨资拍摄一部电影,委实不易。但中国无论如何要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阿诗玛》的拍摄由周总理亲自把关,准备送到国际电影节参赛,这是中国展开积极外交的一项举措,电影是世界性的语言。 《阿诗玛》女主角的角逐自是十分激烈,对于杨丽坤来说,这一角色可谓唾手可得——她在《五朵金花》中表现出色;她是彝族,她就是“阿诗玛”。但她始终钟情于舞蹈,在大理拍摄《五朵金花》外景时,她就常常和其他几朵“小花”偷跑回屋里,把门反锁,躲在里面过“舞瘾”。《五朵金花》成功后,长影厂有意留她,她谢绝了。那双极富魔力的“红舞鞋”,一旦穿上,就注定终生旋转。 《阿诗玛》的女主角几经周折有了人选,交给周总理审批时,总理说:“还是杨丽坤好。” 电影第一场的试片拍好后,送到上海去冲印。放映室里气氛几乎凝固,丝丝地机转声,一会,银幕上跳出蓝底,黑场,台下一片寂静。黑场。寂静。 ——“杨丽坤是电影界一颗透明透亮的明珠!”有人打破了寂静。 ——灯光大亮,掌声雷动。 成了!那是击穿银幕的美,那是“一闪”之间的征服——几乎就在杨丽坤第一个亮相定格时,人们心中就笃定地落下了这一锤! 1964年,《阿诗玛》拍摄完成,谁也没料到,这部多少人苦苦酝酿出的电影竟然胎死腹中。江青审过样片后,淡然一句:“这是什么?这不是宣传‘爱情至上’是什么?不是搞‘封资修’又是什么?” 死刑判决——《阿诗玛》没有公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作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作品,受到全国批判。暴风雨一般的批判无疑将她一掌掌推到了千仞绝壁之上。在她身边,只有一棵枯瘦零丁的小树,她紧紧抓住它——那就是她苦楚坚涩的爱情。 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喧嚣得怕人,即使相近相亲的人,彼此却听不见心音,他们这一对才一见面就大吵大闹;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黑得怕人,生命的相拥如同痉挛,他们这才撕扯扭打…… 这一切传到了磨黑的家中。杨丽坤的哥哥来把她带走了。临走,她恳求哥哥,再让她见他一面,没有得到允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最黑暗的一刻,她那如水明澈的头脑如何被一道魔鬼的闪电撕裂…… 磨黑的青石板小路。她曾经从这里走过一千回、一万回。天下着雨,雨点打落在青石板上劈啪作响。邻居隔着纸窗看见,杨丽坤曳着长裙,仰面向天,她双臂僵直,疯狂地撕扯着灰色的雨幕,从街头舞到街尾,街尾舞到街头……那被雨水冲刷过一千次的青石板路不再记得她幼年时候留下的脚印了…… ——曾经,蹒跚的,歪歪斜斜的…… ——如今,狂乱的,比雨点还急骤的——脚印。 嘶哑的狂喊回荡在雨中: “你们懂什么?你们批?你们配?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鲜花’,什么是……” 末日形体课 1968年底,杨丽坤回到了昆明,看上去她很平静。关于“杨丽坤疯了”的传说仿佛只是一次错误的“提词”。 仅仅一个月,逆风突起,“划线站队”黑云压城。14年,再复杂的舞蹈队型,她都没有错过位,这次她却被判定“站错了队”。逐进“牛棚”,严刑逼供,强迫劳动,她的交代只有一句话:“我没有错。”一天,工宣队点名,“请罪”行列里没有杨丽坤,一时大乱,有人来报告:“她在云大……” ——云南大学操场的讲台上,杨丽坤挥舞着拳头在高喊:“你们 是伪君子!口口声声执行革命路线,实实在在欺骗群众,革委会主任‘一碗水’端不平……” 台下没有观众。“正直”退席,铁幕紧闭,一次遥无期限的“场间休息”。 赶来的工宣队将她绑走了。 云南民族学院。傍晚,空空荡荡的礼堂里有歌声传出,有窥视者从门缝里看到:杨丽坤披散长发,赤脚,在昏暗的舞台上边舞边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完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歌声幽灵般盘旋在礼堂上空,就像打开了魔鬼的音乐盒,她将这个歌剧《白毛女》的唱段重复再重复:“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当最后一线天光在这歌声中窒灭,昏暗中,她伏在舞台正中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下,嘤嘤地哭诉:“毛主席,我想你,我想你……” 1970年,杨丽坤作为专政对象被押解到羊街农场劳改。团里正在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时的杨丽坤已经被永远地放逐出了“人民的舞台”,但芭蕾舞,始终是她心目中的圣殿,是她没有圆成的梦,曾经,有多少次,她偷偷对着排练厅的镜子,模仿芭蕾舞的动作,划出一串串优美的弧圈……如今,在她破碎的头脑里,那梦的残屑仍在闪光…… 每个周末,她一回到昆明,就跑去看演员们排练。她缩在大厅的后排,眼睛紧追着演员的舞步机械地转动,有人做错了动作,她就指着呵呵地笑…… 杨丽坤的“谵言妄语”被逐层上报,最终的定性:“现行反革命”。也有人在下面为她说话:“她说的都是疯话,疯话怎么能作数?”但那个比赛疯狂的时代,如果有谁比疯子更清醒,他就注定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几百人的批判大会。四周贴满“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丽坤!”的标语,她被人押进会场。她只觉得一阵眩晕——这间她最熟悉不过的排练厅,霎时间变成一片血海,无数只拳头滚石一样砸落,一阵阵口号像巨浪将她卷起,在崖石上摔得粉碎…… “立正——”“群专队”的队长喝道。 杨丽坤并不正视他,她挺直身体,右脚的脚尖绷起,在地面上轻轻划出一道四十五度的弧线,定住。这个似稍息又非稍息的动作惹恼了队长,他再次喝道:“立正!”她收回右脚,两脚成六十度分开,脚跟轻轻提起,身体上举,下颌抬高,目光下垂,像水面上一只正要起飞的天鹅……穿过那密不透风的人墙,她仿佛再一次看到了镜中的自己……那是她的第一堂形体课,老师在帮助小女孩们纠正动作:“……抬头,下巴低一点儿,好!挺胸,收腹……” “叫你立正,聋了,你!”有人从背后踹了她一脚,她一个趔趄,还没等站稳,啪!她回身给了那个人一记耳光。大厅里一片寂静,仿佛落入时空的断层…… “群专队”七八个人一拥而上,将她打翻在地。 杨丽坤家里人在绝望中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批复:“对杨丽坤的问题要慎重处理。” 1972年,杨丽坤去往湖南精神病院进行康复治疗。 数年后,“四人帮”粉碎,“文狱”开禁,人们才在银幕上看到《阿诗玛》,迟来的光焰依旧明丽照人。《五朵金花》盛开不败,歌曲传唱不衰。提起云南,人们会说:“那是‘五朵金花’,‘阿诗玛’的故乡。”“五朵金花”,“阿诗玛”至今仍然是,将来也必定还是云南最响亮的“品牌”。 在这个“品牌”的时代,是否有人去研究这一真正“名牌”的历史 . 以上仅对历史上一起著名的毁版事件作忠实的记录.(昆明日报西部周刊特约供稿 ) |
| 原文2000年8月13日 发表于昆明日报,西部周刊 浏览:2100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演艺明星纪念园
演艺明星纪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