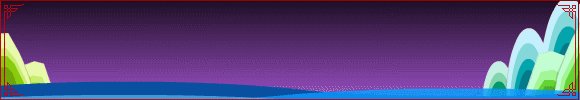叶公回忆录第二部分之青年与流浪-- 3
叶禄群
|
叶公回忆录第二部分之青年与流浪--
作者:叶禄群 http://yeluqun.netor.com …………………………………………………… 青年与流浪 1921年,水寿15岁,二叔怜爱水寿,正月廿三日,我村的年例节过后,介绍水寿到文林村陈学艺家拉风箱熔铜,兼学做铜锁。 每天能吃到稍为多点米的稠粥了,隔天可能还有饭吃,到墟日的晚餐,除青菜外,碰到好运时,还能吃到鱼肉。只是,每天早起四点,晚睡十一时,夜间睡在长板凳,蚊子多得几乎能把我抬过别人家里,自己为了活命,惟有忍着痛苦,任由蚊子吸吮。 九月学成归家,就在家里搭炉替人加工铜锁,别人有气力的,每天能加工三二十把,自己没气力,只能加工十来二十把,哥嫂坐在旁边看视,每天做到晚上12点,哥嫂叫去睡,但是要定时交货,怎敢早睡?每天能获工资二三毫,可籴大米两升。嫂嫂见水寿辛苦有收入,每晚淘碗米饭给水寿。 从来万事不由人,1922年三、四月,广东大小土匪军阀,为了扩张势力,割据地盘,战争烽起,笼罩粤海,往广州的水陆交通梗塞,铜锁没人收购,文林数百家停炉解馆,水寿又重新拖着黄牛,割草拾粪。 水寿从小很少参加田地工,六月工忙,嫂嫂借猪骂狗,冷嘲热讽又来了。水寿由于性子急燥,一溜烟跑到南盛黄岭村替人插秧,别人会驶牛铲秧,每天八毫,水寿只会慢慢插秧,折半得四毫。七月十四,工作完毕,旧俗“做秧了”,老板杀鸡宰鸭,大吃一顿,留水寿在彼处放牛,每日两粥一饭算作工资。 二姐每次回家探望,不见水寿,埋怨哥嫂。后查悉水寿在黄岭放牛,二姐冬至日往合丫村探五姐,姐俩跑到黄岭村把水寿拖回见哥嫂,二姐见水寿身体胜于前。二姐好言安慰:水寿如今长大了,不要乱跑,好好在家跟哥嫂种田,待我回去求姐夫带你去高州店里做杂役。 后来姐夫果然同意,过了年,哥哥拣个好日子,年初五送水寿到高州。姐夫见水寿“鹑衣百结”,即从货架挑了旧衣两套与水寿,水寿头发长了,第一次到理发店请理发师理发。 在姐夫店里,每天担水扫地,烧茶、学煮饭。在亲人姐夫身边,衣暖饭饱。见夜晚灯光明亮,又想起自己的旧书和纸笔。正月廿三回家过年例,哥嫂和三个姐姐见水寿衣裳整洁,仪容光彩,笑口合不拢。廿五日,捡起旧书,拿回到店内,晚上就在明亮灯光之下,写读起来,可是那些旧书,塾师从未讲解过,书中内容,连字义也不懂。 店中伙计许益教打珠算,不数月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右邻广丰店伙计蔡復生常过来玩,教我读唐诗和看小说,自己逐步能看懂其它书藉了。 自己认定将来前途出路,惟有这一条,决心从商界打出路。加上努力自学,各样都有点小进步。 其时土匪军阀吕春荣主政高州,自封镇守使,为了敛取民财,大开“烟、嫖、睹、吹”四门,后街变曲巷,书院作勾栏,笙管楼台,歌声彻耳。其时高州夜晚灯火,赛过“烟花三月下扬州”,姐夫逐渐沦落在花丛中。 1924年,从广州来了个全部是女子的“群芳幻影”粤剧团,演员百三十人皆妙龄少女,在白衣庵前搭大戏院,可容1200人,一连两个月,通宵演出。高州人第一次见到电灯,五颜六色,光怪陆奇。有台上配乐、舞台背景变幻,由女子演戏的,过去都未曾见过。 “群芳幻影”剧团拿手好戏有:“夜吊白芙蓉”“宝玉哭灵”“偷祭潇湘馆”等等。轰动高、雷(高州雷州)和两阳(阳江阳春)。 引得一班王孙公子,挨肩擦背,千里到此,塞满高州所有书院,旅馆。白天,演员们逛街,浪装艳裹。晚上登台演唱,横送秋波,有些戆佬(戆大、神经不正常者)早已醉倒石榴裙下。其实,蛤蟆休想天鹅肉!贫苦居民,都要洗净身上旧衣,拿到当铺,取钱看一二晚。 五月,土匪军陈风超赶走了吕春荣,在冼太庙前公开演唱,我看过二、三晚,也是自己平生第一次看到有电灯配景的台上女子演戏。 从表面看高州,好似繁荣欢乐一片。其实,真的是人间地狱,许多青年男女,在这戏班和当时丑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走向了邪路。 高州后街,清歌妙曲,呼炉唱雉,通宵不休,那班挥金如土的人,的确“喜看橲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姐夫早已乐在其中。一连两个月,流连忘返,店内生零落,顾客稀少,买光吃光。此时,姐夫醉醒矣,归家,父母不肯添本,新债无人相信,旧债频催。 姐夫走投无路,只想着个“睹”字,谁知,屡战屡败。家里闻知,翁姑派二姐来高州,企图控制姐夫外出,但结果恰恰相反。听说,姐夫一夜之间,被麻雀(麻将,高州话有人叫“麻雀”)啄吃一百多元,二姐住下两个月,泪水流干了,一气之下背着精卫(姐姐的大儿子)回家去了。 将届年终,店友许益,虽是多年伙计,看到店里生意难以恢复,早已跳槽别家。姐夫和水寿守着空店到1925年3月,看看无任何转机,只好将残存商品分作两担,挑回金塘摆故衣摊。 水寿又回到家里跟哥嫂耕田,想来是由于水寿命蹇时乖,背运鬼累及姐夫。 1925年3 月回到家里,此时的水寿,不是往日的水寿了,已知道大半做人的滋味,在家又怕惹嫂嫂烦恼。 四月底跟公馆的陈光初、麦华初到安铺找打铜工做,到安铺不久,入安铺西南十八里之鸡炮墟陈泉兴打铜店内。 此时,自己长大了,觉得水寿之名太过俗气,自己想更换名字,想了又想,改名为叶天予。 该店名为打铜,实际是替土匪军队翻制子弹,生意十分兴旺。每日咸鱼青菜二饭一粥,初二、十六两天做“牙期”,有酒有肉,每月工资四元。每月下来,居然有些少零星贮积,寄给哥嫂。 结识了一本地人袁益甫,与他结为异姓兄弟,袁长二岁,呼之为兄。袁是店中找原料介绍顾客的人。 1926年秋,张发奎将军率国民军南下,一个多月,肃清高、雷、廉、琼下四府的土匪军阀。善后绥靖地方,捉拿翻制子弹头子,陈泉兴老板逃跑了,我自己也跑去袁益甫家暂避。 袁家滨海,距安铺30里,全村30馀户,尽是泥墙草瓦,人口百二三十,无一个读书识字。走上海堤向西一望,一片汪洋,无边无际,波涛汹涌,白浪滔天,初看心里惧怕。 村民生活,以鱼为主,农为副。吃的半咸半淡水,赤米粥饭,我住一间小泥楼,早晚由袁妻妹送水楼下,叫声阿哥洗脸脚,畏封建羞,向后跑了。 义兄益甫已婚,父殁母存,有个三妹,五叔年约35、6岁,无子有二女,六叔一子一女,同住一家。五叔忠厚,主持家政,三妹在家专结渔网,技巧冠全村。 在小泥楼住下,时逾三月,五叔常来坐谈,还不知他的内心,自己心中烦乱,恐怕逐客令下,曾三次向义兄告辞返家,却被义兄真诚挽留。五叔知其意,一天晚上登楼坐谈:“天予哥,在我家住下二三年,保证养得你饱,你家无父无母,何必辞归,我怜惜你年青奔波零落,见你眼光伶俐,会写会算,我本村有二十多个适龄入学儿童,设立个书房,请你做先生如何?”说至此,欲言又止,只是微笑对着我,坐久笑说:“天予哥,我想将来把三妹与你成婚,保你一世不用辛苦,有吃有穿。”当时,自己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是说,兄妹之间,于礼不合,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推辞。 五叔离去后,想想五叔刚才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心头卜卜乱跳,一夜不能入寐。 原来,三妹,年十八未字,身材中等,皮肤微赤,常穿一双孔花皮拖鞋,虽荆钗布裙,杏眼和笑口,亦是倾人。想到自己家贫,又无父母,感怀身世,将来必不能娶妻成家,五叔的话,亦未必会成为现实。只好半信半疑,对三妹自己也有几分在意,不如暂且住下,观察五叔态度。 日间无事,与益甫二人,时出安铺玩玩,时到海边堤围捉蟹,倒有兴趣,只是身无分文,思念哥嫂、侄儿。 在义兄家住下七个月,五叔以前所说的话,并不见提及,自己心烦意乱,只向义兄又辞,五叔又来劝说:“天予哥,不用心急,学馆不早不晚,难于成立,你暂且住下,秋收后我打算拿一百几十元,你同益甫去安铺西街尾开一间杂货铺,专做我围田(村)生意就够了。让三妹到店里帮忙做饭,将来成婚,店子和三妹都是你的。”自己虽然半信半疑,但是身上无半文,只得又住下。 八月初,兄弟二人出安铺。在一间鸦片馆内,遇一合浦山口人,年约四十馀岁,自称沈某,原来沈、叶祖先同是兄弟,封建时代,叶沈两姓,不为婚姻,故呼兄唤弟。说话很是投机,彼自言二个月前,到广州探族兄─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当时广东财政不统一,金融各地不均衡,邮汇困难,载和托彼带省钞二三千元返合浦,交给载和兄三老爷,时市面流通的是白银,纸币折银三成,赤坎却能使足水,有乡亲在赤坎开合济押当,存下很多断续故衣(旧衣),今向广州湾(现湛江)赤坎合济押买回合浦出售,转兑白银,交载和之兄……。当时,自己听到故衣二字,即说,我曾做过故衣生意两、三年,对故衣颇为熟行,能分贵贱,每件评定价格,贴上自己知道的暗码标签,任何人都可以做售货员。沈听大喜,立即邀请同往广州湾(现湛江)赤坎,却被义兄阻挠。三人挽手同到忠义街醉月楼晚饭,引去鸿兴行过夜,当晚三人约定,借我与沈兄三个月,年终送返安铺交还义兄。 翌晨,同益甫急步返围田,辞别袁母、五叔、六叔,收拾行李。 袁母、三妹送出村缘,五叔、六叔送上海堤,兄弟二人下快艇,扯帆箭发,下午三时抵安铺。沈已买好四点车票等候,安铺─广州湾。东西相距110里,位于雷州半岛之葫芦口。当晚,抵赤坎住大新街尾合济押当(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沈带我出街,晚上行到最骯脏之牛皮街,看那楼上穿着衬衣正在涂脂抹粉的妓女。 合济押当对门正是赤坎有名的“大新酒店”,楼上女伶,清歌妙曲,通宵不绝。二十馀天,将二千多元的故衣运抵安铺,转船运回山口墟,评出价格,贴上标签,忙了七天,放到各墟,一个多月,尽行沽清。沈带我往沈载和家住五、六天,载和兄在吸食鸦片,每到夜间12点,吃鸡粥睡去。彼家工人婢女不知有多少,早晚鲜鱼、猪肉、鸡鸭,天津露酒,式式俱备,莫怪唐人白居易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回到新墟,沈叫我到他药店帮卖药。十二月初,沈拿出故衣,留下较新的一套,光银六元,派人送我返安铺。自己去寻找高州同乡,打扰二夜四餐。 在安铺踌蹰徘徊两天,心似辘轳,不知走向那条路才好,回见义兄吗?五叔的话,必不轻易实现。想着骨肉哥嫂,隔别将近三年,不如暂且归家,于十二月廿六晚到家,将四块光洋双手递给哥哥。 合家欢喜,过年杀鸡,兄弟畅饮。新年二姐来探,一眼看见水寿,欢喜流泪,笑口合不拢,嫂嫂在旁笑道:“如今还水寿给你,你看六叔,完全变了相,穿鞋踏袜,好似亚官仔。”二姐劝水寿,今后千万不可外出远游,免哥嫂二姐忧心挂念。 二姐并向哥嫂提出建议,早日替水寿寻找婚姻,成双结对,不使水寿当浪子,哥嫂听二姐一番梦话,相对而笑。二姐又说,水寿婚姻若成就,我愿帮助六十元,劝五姐出三十,石碑三姐出十块。后来真的有人拿了生辰八字来,哥哥拿了我的八字,请邻村八字先生合命。后来如何,却不知道。水寿在家闲闲散散地度过了两月,清粥老实难捱,没有旅费,回安铺不得。那时已是1928年,水寿已经22岁,母亲去世已十年。 三月初,跟朱瑞往高州大井开辟公路,每日工银三角二分,除伙食还剩二角,工作虽辛苦,过着山寮大房小集体生活,白天大叫大唱,倒有兴趣。大井至良德,数月竣工,又上东镇怀乡,开辟信罗公路。 1928年十月到达怀乡,工地离怀乡20里,怀乡至贵子路段,全程约百里,有个施工总监,乃信宜东镇墟人,是个破落地主,叫李爵一,常来工地检查路基标准规格和开工人数,每见我休息时就在地下划字,与别人好像有些异样。一天,李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多少书?”我一一敍述给李听。 不几天,李拿来丈竹一条,对我说:“叶天予,你不用锄坑挑土了,帮我检查丈量路基,检查标准、规格及附近三个小队的开工人数,每隔三天,写表汇报一次。拿到水口田交我,每天补工半日与你。”自己一听,自然喜欢,竟然当上了小小的施工员了,每天有补助银二毫,同时结识了一些小工头和工人。 1929年八月,该路准备通车,解散工人,李叫我挑选壮健人员,重新组织养路队,住在怀乡贵子段中间之涌口村。养路工队三十人,我当工队长,每天能吃一二个空额,比小施工员还胜一筹。但是,自己挥霍也大,很少寄钱给哥嫂。 1930年五月,养路队解散,回到镇隆。那时,振元五哥在镇隆义和京果行当杂役,福元七弟在开小茶室,查问家中哥嫂情况。自己乘车下高州,回家探望哥嫂。住了几天返回镇隆,时信(宜)、西(广西)公路已测勘标志完毕。由镇隆至北界全程50多里,拟定底价8000元,采取投标包工办法。 李爵一以6000多元中标,又将全程分为七段,由包工头再行复标。当时自己标得一段,1300元。全程约2里,住北界墟尾。 到1931年二月,李因挪用亏空,旷发工资,我的工人散去大半,但合同四月底交路,工程未及七成,催李多方设法,陆续发给工资伙食。最后李还欠下四、五十元,经数次去东镇找寻,不见李面。三月底方才见到李,李拿煤油二罐给我作抵押。 当晚乘车下镇隆,时福元茶室已停业,夫妻守着空店,妻子将分娩,无盘缠回家,谋之于我,即将煤油一罐与他,令其妻先回家,其妻四月而生振兴。 自己回北界,交路已过期,李千方百计交来伙食费,陆续发工资,拖至六月底,连伙食都没了,还欠工资四五十元,自己因睹亦亏空了二十来元。行李被工人扣住,无奈去东镇寻李爵一,两天见不得面。 守到第三天中午,仍然无结果,只好扎紧裤带,急步下镇隆。抵城已入夜,从天亮到此,滴水未下肚,蹲在城门口坐地。遇一警察前来查问,我将遭遇告之,警察问我家住何方、姓氏。说起来由,与警察乃同姓族兄弟也,警察带我回他住处,招待一宿二餐。 翌晨知福元弟已归家,见振元五哥,不敢述说原因,快步下到高州,时已二三点。徘徊观望,归家无面见哥嫂。胡乱行走,步入后街,见北园书院门前挂一联:广东新兵招募报名处。 忍羞进去报名,但体重不及格,不纳。自思:今日不是异乡沦落,而是近地落魄。无奈向南而行,到达新村铺,路店已关门,虫声寂寂。再行抵家,时已十一点。叩门呼兄,一天走了百三十里,容颜憔悴,哥哥见状,又怜又恼,煲粥吃饱睡去。 这次回家,与往日不同,孤身只影,行李又没,当然嫂嫂眼睛泛白:出去呀!做千九千十,又要回来吃哥嫂。不数日,嫂嫂常借猪骂狗,自己气愤,和嫂嫂争吵三四场。日间吃两碗稀粥,去看二叔磨豆腐养猪,自己想着,此回确实无路可走,唯有去当差路一条。 |
| 原文2011-12-31 发表于http://yeluqun.netor.com 浏览:1556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