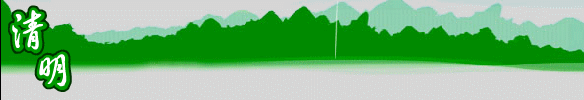自传(续114)交易
赵铁良
|
交易
然而学院“反派性”的声势这时也越来越大,已经听说要以院务部、训练部等单位为主,吸收其他单位的人参加召开几个大会,还要在大会上指名道姓的批评一些人。我心里对这样的方式已经感到极其厌恶,于是我对这个“运动”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并且不准备参加。 但我想躲,有人却偏偏要找到我。曹政委就找上了门,要叫我参加院务部召开的会议。我问什么内容?曹说“阎登修在院里散布对党委的不满,纠集、串联院内甚至院外的部分人,有政治教研室的高堂深副主任,郑树人,还有你们室的黄建……,向上级写控告信,搞得学院不安宁。这叫什么?这叫派性,叫非组织活动!现在就是要消灭这种派性。希望你站在院党委的立场上,揭发这些人在文革期间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现在对院党委不尊重的行为,并在这个会上表态。” 我说“首先,您是老首长,老红军,又有战功,我是很尊重的。但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却不同意这种搞法。小会斗,大会批,这不还是文革用的一套么?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又掀起来,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伤口上撒盐!不错,这几个人是燎原纵队的,该组织在文革刚一开始也做了一些错事,但他们存在的时间不长,仅半年就垮台了。他们立即也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斗争,被发配,被揪斗,死了6个人……,对5.16、5.17,你只字不提,他们可是把学院的领导和各个层面的干部斗了个遍啊,后来又个个升了官。这些事,本来不提也就罢了,现在把这些又搅起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更伤感情!” 曹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耐心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行么?他们串联,写联名信是有些欠妥,但党章上并没有说这是非组织活动,而且这是党员的权利。所以因为这个事你摆不到桌面上来。另外,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不要和派性扯在一起,更不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你这样搞,学院会更不安宁的!” 曹说“不行,毛主席说要在斗争中求团结,对他们不能说软话!”我说“那我不赞成,也不参加。”曹说“给你三天时间再考虑一下,考虑好了找我。” 隔了一天,院务部政委、部长找到了我,说“老赵,听说你要调到院务部来呢!我们欢迎你!”我说“前天曹政委找我了,但没有说这个事情。他叫我参加一个大会,我拒绝了。”接着我说了对这个会议的看法。他们听完说和我有同感,但曹一定要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说“这个会肯定开不好,非乱套不可!”部长(原福州军区后勤部长)说“我也不参加这个会。”政委笑笑“参加嘛还是要参加,说多说少,还不是由你。” 于是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层中分歧就很大。后来我又听说不少老同志都接到了参会的通知,但也不准备参加,象郝宪文,苏欣等。 我于是又找到杨院长反映意见。我说:“是批斗还是说服教育,是消炎还是撒盐,究竟那个办法好?”杨说“当然还是消炎好。”我又问“曹政委这个办法行么?”杨说“这是院党委定了的,他们到处乱捅,联名告状。”我说“如果单就这个问题,还是个别谈好。党章也没有说这样不行,这样说来,我肯定不参加这个会。我的理由就是太忙。”杨说“唉,不参加就算了。”我说“我准备辞职,我年龄已经到了。” 杨说“搞教学的还可以延长两年么!干嘛这么着急。”我说“如果有个好环境,我还真打算再多干两年。但再这么人整人,干还有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还愿意找杨院长说说心里话?因为他比较愿意倾听下级的意见。我们搞计算机如果早期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夭折了也说不定。还有一次,他不知是听了谁的谗言,说我们私存手枪——就是那支四川仓库专门给我的报废的用做教学的枪,我跟他说明情况,他开始不听,气的我在电话里跟他大吵一顿。但这位老首长竟然亲自找到我家来,听我说明情况。我说,我们本身就是搞军械的,这支枪,是为教学用的而且是报废的,怎么能说是私存枪支?经过一番解释,杨院长说:“赵主任,我错怪你了。”就凭这,我心里就十分敬重他。 过了三天,我没有去找曹,曹却找到我来了。这次的架势,看来是要摊牌。曹问“你老赵到底参加不参加这个扩大会?”我说“您是不是非要强迫我参加不可?如果是这样,我可参加,但我的发言却不能按照你的意图讲。说不好听的,我可能要跟您唱反调。” 曹一听,说“你如果能够按照院党委的意见表个态,指出写联名信的人是派性行为,那么你当院务部部长的任命就可以宣布;否则就不宣布了。”这时,我才正式知道,要提升我为院务部部长(正军职)。但是听了曹政委的这个话,我感觉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血直往头上涌,我大声说到:“你如果这样说,那我也明确告诉你,这个会我不参加!如果强迫我去,那我肯定和你唱反调!”曹政委的脸色非常难看,走了。 在众多的反对声中,扩大会还是开了,后来我了解到,会议开的很不成功,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参加会议的,学院的老同志很少,来的都是一些年轻的,不了解情况的。会上张冀东副部长公开唱了反调;阎登修发言说,这还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院里这样搞,是违反中央要安定团结,要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精神的;那些年轻一些的人,虽然发了言,说的都是一些摸棱两可的话。曹政委的脸色非常难看,只说了一些目无组织,无纪律,搞的院里不安宁一类的话。就是这个话,也有人顶他:“今天的派性是谁挑起来的 ?不安宁是怎么引起的?是院领导挑起来的!” 会议在极为尴尬的局面中收了场。 后来我问院务部长为什么曹政委一定要坚持这样搞?某部长说,还不是总政的梁敬叶,还有余夏伟他们在后面支持的!如果总政问题不解决,军队几个大部派性解决不了。 这位部长,由于没有参加曹召开的会议,直到去世,还是按照军的待遇,而政委参加了会议,离休时是按兵团待遇,可见曹的报复心有多强。 在我们室副主任的人选上,这时也出现了岔子。由于任君止已经去世,需要重新任命一名副主任。这个事我原来已经跟杨戈江打了招呼,要让孙凭义当。但组织部门来人,提议叫陈教敏当。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曹政委的意思,看来他这个人选人的标准不是人品和能力,而是听不听话。陈教敏,连教学大纲都搞不出来,讲课也不行,如何能够胜任?我说不行,并再次重申应该提拔孙凭义。组织部门的人没有说话,走了。我赶紧找杨戈江说这个事,杨同意我的意见没有变,这我就放心了。因为这时我已经得到消息,学院要随着裁军降格为兵团,人事要有大的变动;杨戈江估计要当副院长,来一个李宏当院长,而杨、曹等几个老的都要下去。所以杨戈江的表态靠得住。 果然不久,孙凭义的任命下来了。 1983年下半年,我写了第二份辞职申请离休的报告。到了年底,终于批下来了。这时我考虑,应该叫孙凭义接我的班,马上任教研室正职。和黄建、徐泽天一商量,他们欣然同意;又和黄村森、苏欣打招呼,也同意。我还为此征求了王卫昌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按照程序把报告打了上去,院里很快就批下来。 但杨戈江找到我说:“你现在虽然离休了,但对于孙凭义,你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啊!”我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我只抓几个主要的事情:课程,抓传统如何与现代化相结合;各门课之间如何有机的安排和衔接;全室的管理;如何联系部队的实际;如何领会军械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的精神及要求等;我还要带他到部队和某部机关去跑跑,熟悉一些情况和人事。”杨对我的想法都表示同意和支持。 从1984年起,我就开始带孙凭义。带他去某部门,带他到下面跑仓库,跑部队;在教学指导思想上,我叫他一定要结合部队的实际,不要跟着后方教研室的核大战理论跑;在教材的编写上,要他因地制宜随时补充新的东西,发现下面有了问题,及时提出新的解决方法,然后组织实验,成功了就补充到教材中;还和他集中研究了计算机的推广问题,加强人力,增加设备……。 曹恩缘在快下台之前,还在做不得人心的事情。比如军械教研室支部改选,他这么一个大政委也要插手,非要把梁关文、陈教敏、韩雨蓬等人选进去不可,他还要来亲自督阵,并把这三个候选人名字放在了前头。说实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老头子到底想干什么。选举的结果,这三个人分别只有三票(估计是他们自己互相投的),几十名党员没有人投他们的票,支部委员最后还是我、黄建、徐泽天、孙凭义、王亮云。曹恩缘再一次闹了个灰头土脸,一句话不说,走了。 不久,院里要调黄建去卫勤当学员队副队长,黄认为是曹的主意,就是不去,经我说服还是去了,但他和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有时到了公开的程度。有一次,院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黄就拿了一个小型录音机去,要录曹政委的讲话,有人制止,黄说:“我要回去好好领会曹政委的讲话精神。”结果就没有制止住。 想想也好笑,一个堂堂大军区级的首长,为什么就和自己的部下过不去?在他身上,我隐隐感到了封建家长制的深刻影响还在发生着作用。虽然时代早已经前进了,尤其是经过文革的这场暴风骤雨,所有所谓的权威都被打倒了,谁还会吃你这一套? 在后来的党员重新登记中,组织部门就不给黄建重新登记。你不登,就不登,我也不找。于是黄建就油印了许多申诉材料向上级的诸多首长到处散发:什么杨尚昆、薄一波、邓小平……,材料中诉说他怎么参加的革命,文革中被关了多少年,到现在院领导还不放过他云云。把个曹恩缘搞得没有办法。 直到曹离休了,黄建才给重新登记。曹离休以后,在学院就没有什么人理他了。不但不理他,还不把他当回事。他的车开在路上,有的干部就是走在路中间不给他让道;有的职务比他低得多的人,也指着鼻子骂他。幸好这时他的耳朵已经聋了,不然还不是每天满耳朵的骂声。一个老红军,晚年落到这步田地,也算是他始终抱着整人思想的下场。 |
| 浏览:1661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