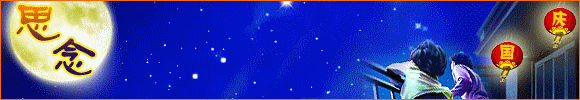《严恺院士》(二):谦逊地征服傲慢与偏见
|
《严恺院士》(二):谦逊地征服傲慢与偏见
二、谦逊地征服傲慢与偏见 1986年10月,荷兰海牙国际机场,74岁的严恺神采奕奕,健步走下飞机,迎接他的,是荷兰人迎接国家元首的礼仪,他这次来参加一项特殊的典礼。 已经建成了众多世界水利杰作的荷兰人,从二战之后,投入数十亿美元,奋战三十余年,建成了又一项世界之最——能够抵御四千年一遇特大风暴的东斯赫耳特防风暴大闸。大闸由62座巨墩支撑,这些巨墩,荷兰人赋予它们以人格魅力:全部用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荷兰人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尊重,他们希望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成为荷兰乃至世界人民的保护神。这些巨墩中一个属于东方科学巨星,名字叫严恺。 大坝给了科学家以荣誉,科学家更使大坝增辉! 典礼也是世界级的:比利时国王、英国女王以及法国总统都来了,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一起分享人类智慧与胆识的结晶。严恺挥笔题词: “Great Wall” on the sea Wonder of the world(海上长城,人间奇迹) 题罢,在梦一样的欢乐气氛中,他的目光望向远方,似乎看到51年前那个只身闯荡荷兰的东方学子,陷入了梦一般的遐思—— 严恺1933年7月从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正遇黄河水利委员会登报招聘防汛技术人员,他报了名,但因为是应届毕业生,没有录取,于是被分配到沪宁、沪杭甬铁路杭州工务段任实习员,这里并没有什么实际工程。10月便投奔当时任湖北省会工程处主任的校友方刚,任工程员。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地区,武汉三镇又被江汉分割,水患频仍。严恺带着学子的热忱,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和防汛工作。他虽然初出茅庐,但充满激情与想象力。他在武汉的第一件作品是为张学良将军设计的汽车轮渡码头,利用江堤,修了一条长长的斜面车道,这样汽车可以直接开上轮船,张将军十分满意。 正好要重修黄鹤楼,要横跨马路修建一座桥。因为码头的成功,所以这座桥的设计任务就交给了他。严恺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设计了一座结构科学、造型新颖的钢筋混凝土刚架桥。这座桥同样获得了成功,同时他的创造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这是一座小桥,不要说是在桥梁界,就是在严恺本人辉煌的事业中也并不起眼,没有人会因为它而去注意它的创造者,但我们实在不应该忽视这座桥,因为这是严恺第一次被直接推到社会的面前,推到他的事业面前,推到他自己的人生与命运的面前。通常这个时候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来的,不是经验与才能,而是一种本能,一种基于性格的处世方式。一个保守型的人与一个开拓型的人采取的设计方式绝不会是相同的。严恺的设计不仅体现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也体现出了他高超的实际运用能力,更体现他大胆的创造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可或缺的。严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他的人生中是不断强化的——他喜欢开创性的工作。这不正是他在《十六字校训》中提出的“勇于探索”吗? 杰出的创造能力正是严恺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创造精神就是面对未知时特别的征服欲望,而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要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一种运用现有的知识基础、现有的物质条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还记得他小时候玩的那种“骑马征战”的游戏,他玩过的游戏应该不止这一种,但他只记得这一种,这正表现了他深层性格中强烈的征服欲。联系到以后的各个阶段,严恺几乎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都贯注着一种强烈的征服欲,他总是带着必胜的把握开始一件事,最后,不到胜利绝不罢休。在学生时代的学习成绩上,他不做第二人;在工作上,他也从来不居人后,不断向前、向陌生与未知开拓,大胆地接受创建华东水利学院的任务就是典型例证;在学术上,他更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之先河,并创立了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等新兴学科。他是我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5年他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各类专家领导小组中都是组长,在诸多世界级的协会中他也是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是组长,而不副组长;是主席,而不是副主席。这是成就,更是性格,一种因为性格而取得的成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翻看严恺先生所有影集时的感受:他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中都留下了具穿透力的眼神,仿佛他从北京的小巷子里就能望见长江大海,仿佛他从“马背”上就能望见大漠风烟。我更无法忘记与他长谈的那些感受:九十岁的世纪老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沧桑历尽,功成名就,但依然胸怀天下,壮心不已。严恺是生活的强者,更是一个胜者,永不言败。 1935年,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决定选拔一名土木专业的技术人员到荷兰留学,荷兰是水利工程的圣殿,学土木的谁不知道这个留学名额的价值?只有一名,Do or die!严恺一听到消息,便立刻从武昌乘船直下南京,并从所有选手中脱颖而出,以绝对优势取得第一名。这样的关口在严恺以后的人生当中还有很多,但他都举重若轻,顺利过关。他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 为了节约时间,他不走海路,而是取道上海→大连→满洲里→莫斯科→柏林→海牙这一条路,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离荷兰首都海牙七公里的大学城,迈进了德尔夫特(Delft)科技大学的门槛。 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是荷兰最著名的以应用科学为主的国立大学,严恺又是第一个跨进该校留学的中国人,形单影只,身材本来就不算高大的他夹在那些高大的白种人中间更显柔弱。德尔夫特科技大学的师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来自东方的陌生人,是怀疑?是询问?是好奇?说不清楚。 入学要进行甄别测试,一考专业,大家不得不对这个小个子黄种人刮目相看了:成绩优秀,免除后面的预备考试和候选考试两大关,允许直接参加博士(工程师)入学资格考试。当然,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严恺虽然英语功底很好,但荷兰语却是一窍不通,而且,荷兰语与英语的差距很大。没关系,谁让他是严恺呢,就凭着他的英语功底和超强的记忆力,跟着一个荷兰语的私人教师猛学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他竟然能听懂直接用荷兰语讲授的课并且能做很好的笔记了。 语言确实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尤其到了国外,你不懂人家的语言就如同文盲。严恺不仅很快学会了荷兰语,而且还主动放弃休闲娱乐,利用假期跑到德国去学习德语,后来还自学了法语和俄语等。 1936年暑假,别人都休假去了,严恺听说柏林大学有专门为外国人学德语而开设的为期两个月的短训班,他便一个人跑到了柏林,时间毕竟有限;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竟然一下子报了初级班和中级班两个班,上下午连轴转,早晚再抓紧复习。才学了一个月,许多人还没有入门,严恺却已经感觉到学习德语的快乐了。一次,女老师提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然后面带宽容的微笑看着一群满脸茫然的学生,或许她并不准备有人能答出来吧。不料,严恺却站了起来,而且准确地回答了问题。这位女教师惊讶了,但很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的?”严恺没说话,谦虚地笑笑,但这个谦虚的笑容却赢得了老师的欣赏与同学们的敬重。初级班结业考试,他考了第二名,老师和同学都为他鼓掌,他自己却一心懊恼,要知道,他是不做第二人的人呀。他没有为自己找理由:那个考第一的罗马尼亚女同学原先就有一点儿德语基础。不过他也能找到一点儿平衡:中级班里他考了第一! 《文汇报》1980年9月23日在《征服江河的人——记著名水利专家严恺教授》一文中饶有兴致地报道了这件事,那是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需要这样的精神。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精神。我在河海大学采访的时候,就不止一个人充满钦敬地说起严恺先生学外语的故事,大家都把这归结为他超凡的语言天赋,但严恺先生却谦虚地说自己靠的是勤奋。他对学外语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他说:“其实学外语不难,就是靠两条,一是不要命,二是不要脸。不要命就是你得背,得拼命地记;不要脸就是你别不好意思,得多说,尤其是跟外国人说,反正你水平差,别怕人家笑话。”是的,在知识面前,我们都得有这种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有一次严恺接见一个英国代表团,私下里用英语跟他们说了些话,英国人非常惊讶,说:“你到英国学习过?”严恺笑笑,说:“没有,我只去过英国几天。”英国人赞叹说:“你说的是很好的英国调呢,真不简单。”严恺心想,我说外语不像外国语,那还叫什么?1987年9月,他主持召开的“发展中国家海岸和港口工程国际会议”上,在致闭幕词时曾用中、英、法、德、荷、丹麦、阿拉伯等语言宣布:下届会议将于1991年在肯尼亚举行,那时再见!台下响起了一阵阵掌声,一片欢腾。 作为一个科学家,严恺的行为确实洋溢着科学的精神,求学也是这样,他不满足于课本知识,更注重实际运用,所以他在荷兰读书期间就非常注重实地考察。荷兰虽然面积不及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当时人口也还不到一千万,但它西、北两面临海,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荷兰人在与大海争夺生存空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水利工程奇迹。严恺一有时间就扑向这个大课堂,沿着1075公里的海岸线实地考察荷兰的海港、水利建设,千方百计地与德尔夫特水力试验所联系,到所里参加他们的模型实验,获得宝贵的直接经验。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三年勤学,1938年夏,严恺面临最后的毕业面试了。 主持面试的是van Mourik Broekman教授,以博学和严格闻名,很少有人能第一次就赢得他的满意,因为面试不及格而不能毕业因而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面对他的学生大有人在,学生们既诅咒他,又不得不尊重他。严恺早有耳闻,有点紧张,但并不害怕,因为他自信,也因为他遇到的严师还少吗?宁波四中的老师不用说了,就是唐山工学院的老师也是一个比一个严厉,教力学的罗忠忱先生,不论你用什么方式解答,只要结论是错的就绝对零分,没有任何商量,两次不及格,double fail,开除。罗先生的话现在严恺还记得:你们是搞土木工程的,一个小小的错误都是大量的金钱与血汗啊! 叫到严恺的名字了,他反而不紧张了,相反,他倒对这个威严的主考大人和他的方式有点儿喜欢了。他看了看那一排著名的学者教授组成的智慧的大堤,要知道,这才是荷兰人真正的水利工程的精髓啊,能看一眼,也是荣幸呀!严恺整了整领带和大礼服,迎着主考大人Broekman教授的目光向他走了过去。 先是一些常规性的问题,严恺用荷兰语认真应答,准确,流利,自然,如水泻地,“长堤”有了点儿动静,一个个难题便接踵而来,严恺依然面带谦虚的微笑,认真作答,Broekman一直看着眼前的这个对答如流的东方学子,他不奇怪,相反,他只是觉得这个学生就应该是这样,他甚至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这样。最后,轮到Broekman教授自己了。Broekman教授提的问题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广,有的甚至超出了考试范围,严恺都—一回答了,当答了后一个问题时,Broekman教授的眼睛亮起来,面露喜色,跟严恺开玩笑地说:“真遗憾,我无法再见到你了!” 一句玩笑,严恺却不无感伤。不是因为三年汗水付出太多,也不是因为离开哥哥姐姐太久,也不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告别太快,而是因为这一句玩笑里包含着Broekman教授对他的欣赏——三年的异国他乡,因为家国贫弱受人歧视太多,太多,在终于能够骄傲的时候,才感到这一颗坚强了这么久的心其实是多么脆弱。 依然带着谦虚的微笑,严恺对这一道智慧的长堤真诚地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去。Broekman教授看着这个东方学子的背影,忽然觉得他穿礼服打领带的样子其实很好,很帅。 但严恺接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脱下这件借来的西方礼服,穿上自己的衣服,奔向东方的祖国。 |
| 浏览:1618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
 网同院士纪念园
网同院士纪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