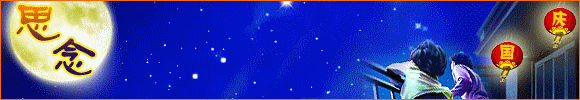《严恺院士》(三):水利抗战
|
《严恺院士》(三):水利抗战
三、水利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战的消息传到荷兰,严恺满腔热情地跑到中国驻荷兰公使馆,询问如何回国参加抗战。公使馆的人说:“你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但你现在是留学生,你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更多的知识,要知道,前方抗战,后方生产,要搞好生产,知识可比枪炮还重要啊!” 严恺懂得这个道理,但心里的委屈与愤怒却无法挥去,几年来,身在异乡,作为弱国子民,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他无法忘掉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那次奥运会,当时他正在柏林学习德语,听说中国队派了一支不算太小的代表团参赛,海外学子都非常激动,严恺与几个中国学生贴出巨幅告示,组织啦啦队,训练口号:“世运招待会,组织啦啦队。歌调要新颖,口号必叫对。一人首先喊,大家一齐随。鼓励我选手,夺得锦标归。”兴致勃勃来到赛场,可赛场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头脚冰凉:由戴季陶出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人倒不少,有一百多号人,可一比赛,刘长春的100米预赛就被淘汰,符保庐的撑竿跳成绩是3米15,比当时的世界纪录低了1米还多,铅球选手、号称铁牛的陈宝球只推出了12米多……。比赛比赛,可赛得的只是台上的一阵阵哄笑。严恺旁边一个兴致勃勃的观众注意到了他垂头丧气的样子,主动搭话说:“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看你像是日本人。”这句话大大地刺伤了严恺的自尊心,当然,这样的委屈也不是第一次了,要是平时,他也就忍了,但今天也许是赛场上的气氛太激烈了,严恺涨红了脸,大声说:“胡说!我是中国人!”说完,愤然离开了看台。他知道,国家要富强,得靠每一个国民为之奋斗,他默默地努力学习,心想,祖国总有需要我的时候。 如今,他终于学成归来,可以报效祖国了。1938年,在他取得了荷兰德尔夫特大学土木工程师学位后,于11月乘上马赛到上海的邮轮,他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啊:祖国,已经仅仅是时间上的距离了。 由于上海已经沦陷,于是到了越南西贡停泊的时候他就改乘西贡到海防的轮船,在海防换滇越铁路前往昆明,一方面是因为二哥严铁生正在昆明,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也已迁至昆明,他要去中央研究院,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尽快发挥出来。 严恺心里急啊,国家正处在抗战的艰苦时期,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能不急吗?! 到了昆明,找到二哥,一安顿下来,严恺立刻找到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但研究院却无法很快给他提供合适的岗位,正好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需要工程师,他只是急着工作,心想反正工作起来再说,就进了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农田水利状况,为水利工程贷款。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滑竿,两根竹竿,再串上绳子,旅客把铺盖往绳网上一垫,两个汉子抬了就走,翻山越岭,竟然走得飞快。后面一个看不见路,就靠前面一个提醒,提醒也是艺术,如果地上有一堆牛粪,前面的一个就唱:“天上一颗星嘞”,后面一个就接着唱:“地上牛屎堆呐”,前面一个唱:“小心别打滑嘞”,后面就唱:“你走我紧跟呐。”严恺一开始坐在滑竿上很不好意思,但在这样的山路上走着,还得有人扛行李,再说到了目的地,他还得跑很多路勘测,就这样听着老乡的山歌,也算是休息一会儿吧。 到了夜晚投宿,可就远没有白天这么浪漫了:虱子、跳蚤无孔不入,咬得你坐卧不宁。 但就是这样,严恺也还是不肯放松,在如豆的油灯下,把白天所考察的项目是否给予贷款的理由和实施方案加以整理,很多时候,都得对设计方案大加修改甚至要另起炉灶。但严恺一点儿也不叫苦,他知道,他所学的专业就离不开艰苦,他这样辛苦地工作就是最好的抗战方式。 但他的身体却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他患了猩红热,皮肤上出现大片鲜红的点状斑疹,口干舌燥,高烧不退,烧得人都迷迷糊糊。幸好治疗及时,再加上他平时就能注意锻练身体,体质很好,终于在一个月的斗争之后,病魔悄悄去了。 身体好了不久,他又开始了艰苦的工作,这样一年多的时间,他跑了大半个云南,对云南的农田水利建设作了规划,而且还自己独立设计了好几项水利工程。1939年初设计的弥勒县竹园坝灌溉工程在当时被视为杰作,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发挥作用。后来,严恺先生成了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这个小小的工程作为大坝主席的起点,该感到荣幸了吧。 1940年2月,严恺接到已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的聘书,受聘为水利工程系教授。这一年他才28岁,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年龄成为正教授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毕竟是著名大学的高材生,毕竟是众多严师培养出来的高徒,毕竟心里揣着以知识报国的强烈愿望,严恺一上讲台就雷厉风行,一个严谨的学者必然是一个让人敬重的师长。他的课丰富、扎实、有创造性,他的要求严格甚至于严厉。1941年,一个兼着三青团干事长之职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缺了不少课,严恺提醒他,但仍然有三门课挂了红灯。眼看毕不了业,就要求严恺,请他将他所授的课改为及格。严恺一板面孔,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没有任何商量!曾任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水利学会港口航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的黄胜先生是严恺中央大学时的学生,他回忆严老在中央大学讲课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说:“我是42年的毕业生,严恺先生给我们讲授水工设计、河工学、港口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等多门课程。当时常有学生轰老师的事,可严恺先生的课却很受欢迎。他教学内容丰富,有新鲜感、有深度,要是记下来就是一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仅使受教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你所教的知识,还能够理解和接受你的思想感情。严恺教授的许多学生都认为严老给予了他们终生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教育者的大成功。1992年10月12日,河海大学聚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中央大学1942届的毕业生,被严恺先生戏称为“18罗汉1观音”的19名毕业生到了12个人,他们从世界各地聚来,聚到恩师的面前,严恺教授唯一当时任教的教授参加了聚会,一场师生的聚会,更像是一次水利的盛会。 遗憾的是时间不长,严恺先生就不得不离开了中央大学。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说是校长,其实是忙得连学校都很少来的。有一天,蒋校长突然一身戎装来到了中央大学,戴着雪白的手套,前呼后拥不说,来了就训话:“你们看看,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严恺早在宁波读书的时候就受二哥严铁生的影响,对蒋介石印象不好。当时二哥写了一篇文章,说蒋介石是新军阀,不想被同事告发,差点儿被捕,逃了上海躲了好长时间。现在,他当然不会去听这样的校长的训话,听同事回来议论,他愤愤地说:“他蒋介石想当什么官不行,偏偏要来当什么大学校长,什么‘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难道他那个样子就像个大学校长?” 严恺先生这样说当然不是什么一时的激奋之辞,二哥的影响,多年国内国外的生活体验,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有深刻的认识的。这就是严恺,纯粹、正直,忠于自我,坚持真理。然而不幸的是,他也像二哥当年一样,立刻被人告发,上了一张阴森森的黑名单。他一气之下,丢下了月薪600元的讲座教授之职,应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李书田先生(曾任唐山工学院院长,对严恺十分赏识)的邀请,前往西安,加入了因为抗战而西迁至此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任简任技正兼设计组主任。 与洪水打交道要比与人打交道简单得多,或许这样的工作更适宜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吧。 然而,面对黄河,严恺的心里同样无法轻松。黄河,激情澎湃的黄河,黄河,多灾多难的黄河。作为炎黄子孙,他的心里有着深深的黄河情结;作为水利专家,他更明白黄河的意义。据史书确切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一共有543年决口泛滥,大的改道就有9次,这在世界河流史上也是罕见的。 黄河是多沙河流,年总输沙量和平均含沙量均居世界大河流首位,它与长江的径流量之比约为1∶20,而含沙量却是长江的3倍,每年将15亿吨的泥沙东运入海。黄河是中国的一道难题,黄河是出给人类智慧的一道难题,它对所有水利专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严恺不怕,相反,巨大的挑战只能更多更强烈地激发起他奔涌在血液中的征服欲望、开拓精神与创造性,面对黄河,他感到了内心有一股战马闻到硝烟的躁动。 作为设计组的主任,严恺身先士卒,艰苦的事情走在前头。在宝鸡峡勘测过程中,他上高山、下深谷,不畏艰险。有一次竟从山坡上滑了下去,幸好下面有一条小沟,这才没出大意外。同事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可严恺自己爬上了山坡,继续向前,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走起路来也是快步如飞,他一小时走7、8公里。有一次走得太急,又要爬山,布鞋小了,挤得大脚趾化浓,他硬坚持着把工作做完。结果医生说太迟了,这个脚趾甲可保不住了。严恺说,那就拔掉吧。说得比医生还轻松。 不久,一项项成果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宝鸡峡水电站》、《渭河治理》、《黄河下游治理》等等。同时,他还完成了重要论文《黄河下游各站洪水流量计算方法之研究》,发表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季刊第一卷第八期上,成为黄河水利研究的重要文献。 1945年3月,当时的中央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决定派人去西北宁夏灌区进行实地的地形测量和水文测验,提出抗战胜利后士兵复员屯垦规划。黄河水利委员会认为这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事,应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派人。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认为这么重大的事黄河水利委员会没有人能办得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人笑笑,说:“我们有严恺。”中央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人一听,当即说:“严恺我们知道,你们有严恺,我们就不跟你们争了。”于是严恺成了宁夏工程总队总队长。 一开始,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些人认为严恺只是一个30来岁的书生,对他能否做好这个总队长,搞好这项重大工作表示怀疑。但严恺没有说什么大话,他把所有的力气与心思都用在实际行动上了。首先,为了行动方便,他租了几辆大卡车,但上车的时候,他把驾驶座边的好座位让给了工程队同志的家属,自己坐在卡车后面的行李上。这一个不经意的细节被那些本来带着怀疑的眼睛看到了,那些眼睛慢慢露出了信任的目光,说:“严恺虽然年轻,但能做到这样,没说的,他肯定行。” 宁夏原来就有一个勘测队,但一个月只能测量几平方公里的地方,照这样的速度,得干一个世纪。严恺把一百多人分成5个工程队,划定区域,分头测量。三个月,一个工程队就完成了测量任务,测量工作总结报到水利委员会。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很惊讶,水利委员会当然高兴:奖励!记大功一次,年底考评,各有奖励,作为总队长,严恺工资连升两级,从460元升到520元。 要知道,任何成绩的做出都是不容易的。一个工程队的下一个目标是贺兰山的深处,队长和队员都说那里几十里没有人家,去不了。严恺什么道理都没讲,打好行李,带了人就直奔大山深处。果然荒凉,果然艰苦,但严恺早有在云南水利贷款委员会的经历,这些苦他吃得了。好不容易找到人家就投宿,卸下门板就当床,第二天一大早就给人家再装上,如果没有人家就露宿大山的怀抱。他这样做,别人还能说什么,干!很快,那些比较艰苦的地方又测量完了。到了年底,测量工作基本完成,同时完成的还有重要文献《宁夏河东河西两区灌溉工程计划纲要》,水利委员会再次给予奖励,严恺的工资再升两级。这一升,就到了600元,已经是简任技正的最高限度,不能再涨了。当初他从中央大学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不知道具体内情的人都说他傻,放弃600元月薪的工作来做460元的工作,但对于严恺,他只想着如何做些实事,做出成就才是重要的。 工资的增长说明严恺做出成就,做出了让水利委员会惊喜的成绩,同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采访的时候,我说:“这件事充分反映了严老的组织能力。”严恺立刻纠正(或者说是补充)道:“还得身先士卒啊!” 回忆中,严恺对宁夏工作的艰苦说得并不多——这也是他一惯的态度,有许多事情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在严老的叙述中总是那样的平静,他甚至很少提那些艰苦的方面。他讲得最多的是水利本身的事。比如这次宁夏灌区的测量,他的兴趣完全是在测量的意义与测量的结果上面,而对工作中的艰苦却说得很少,要不是我一再追问,他可能都不会提起。这使我想起《十六字校训》的第一条就是“艰苦朴素”,严老曾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水利本身就是一件艰苦的事,你一定要有艰苦朴素的精神。”吃了那么多苦却不说,这才是人格中最高的朴素。但我们也看到,他在讲到《宁夏河东河西两区灌溉工程计划纲要》时,脸上充满了特别的光彩,而那种光彩才是一个科学家真正的骄傲。 这就是所有伟大人物(尤其是科学家)的伟大之处,他们在事业面前不仅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而且常常具有一般人所不具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忘我的奉献之中,他们成就了事业的辉煌与人格的伟大。 |
| 浏览:1238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
 网同院士纪念园
网同院士纪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