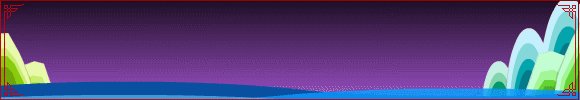我的蒙馆夜学—陈佛光先生
王海演
|
我的蒙馆夜学—陈佛光先生 王海演 陈老师佛光字承,同乡蛟溪村人。幼读四书五经,清政府于1905年停止了科举考试,未参加童子试,未得秀才之名,只是一名知书识礼的读书人而已。 1943年秋七月,经我族两位有识之士的商定,聘他到我荷坊自然村教书,言定半年内每位学生交干谷五斗作为报酬。学生十人共付干谷五担(500斤左右),每天饭食在学生家轮流吃,每家一天,周而复始。 十名学生中两人白天上课,八人白天在田山上劳动,晚饭后才到学堂读书,叫“夜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个。陈老师白天在学堂里(设在荷坊上中芜众家大厅内)代学生抄写课本(当年没有教学书,学生学什么,老师就代抄什么),他替我抄的《百家姓》、《人家日用》等课本,至今仍保存完好。有时老师也砍些毛竹,破篾做点家用品补充一些收入。 学生一到书堂,老师先教写字(练写毛笔字,当时没有钢笔)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学生得带着写字本到老师桌边猜字(认字),老师把学过的生字,用红朱笔楷书写在学生练字纸的反面,老师写一个,学生念一个(此时学生不能看书),如读不准,老师就用戒尺(木质,四方形,长约七、八寸,漆红色,平时放在老师抄书的桌上)打学生手心,错一个打三下,以此严警学生要认真读书认字,牢记读过了的每一个字。接下去就是背书,学生把上回读的背熟了,老师就点读新的内容,老师点一句,读一句,学生跟着读。如果背不下,就不点新内容。让读原来的。对于背书有严格的规定,即读过的内容必须背熟,而且每到初一、十五必须把所学过的的内容从头到尾背给老师听。学生记性有差异,所以学的有快有慢,有多有少。我在蒙馆夜学半年中,已背读过的课本有《百家姓》、《人家日用》、《治家要用》、《米谷豆子》、《增广贤文》、《千字文》等等 ,在十名学生中走在前边的。半年后,堂伯父家发说“一庵和尚替一人修”,第二年就不请老师到村教书了! 佛光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是个纯朴忠厚的人。教我书时,年近古稀,冬天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外套长衫,下霜时脚穿布缝的旧袜子,布鞋,有时提个火笼取暖(他自已做的),缩着身,半弯背,平时戴着老花眼镜,不苟言笑。他曾给我们讲他读书时的故事,以及当地前代人的故事。他说以前读书,老师很严格,所读过的书都背得滾瓜烂熟,否则老师就不放过。他摇头说:孟子,孟子,读出脑屎,离楼,离楼(两篇四书名)背出肠头.......他讲村里上代人与油贩子打赌的事,主人许诺说:“谁能猜中我窑中多少茶油,你买的油就不用付钱。” 陈老师抄书一笔一划,认认真真,教学生读书识字,半年时间只得500斤左右的干谷作为报酬,收入少得可怜,生活多么困苦啊,他是知识份子的代表。新旧社会对比,今天当老师的可谓天上人间了!即使幼儿老师每月的收入也不少数千元人民币,不是多了十几倍的收入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尊师重教 ,教师地位提高了,今天当老师的怎不感到自豪与骄傲呢! 然而就在今天,不少青年人不愿到学校当老师,每年参加高考学生,报名师范专业就少得可怜。这些青年人认为:当老师没有前途,一生贫困,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又遭世人的白眼。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尊师重教的,为师者得到人们的尊重。认为老师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年人成长的指路人,传道授业是神圣的工作,是培养人才的工程师。 自从“12.9”学生运动,打倒孔家店百余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师地位日落千丈,人们提到“教师”笑脸尽收,甚或嗤之以鼻,高尚师德,也就难于寻找了,长此以往,对人材的培养不堪设想啊! 2020年6月 |
| 浏览:380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陈公忠钦纪念园区
陈公忠钦纪念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