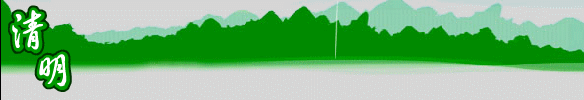苍蝇
小立
|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搞的,我发现我的世界乱了套。
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以及再上一个礼拜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在网吧里泡上三四个小时,我跟各种昵称听起来纯情得发腻以及恶心得令人作呕的人在OICQ上瞎聊,直聊到我们彼此都懒得动鼠标为止。 我给自己起了个很“耍”的网名,然后跑到那些有名气或没名气的论坛里乱回帖子,碰上写得好的就回几句"说的对,哥们儿,我真喜欢这些句子"之类的废话,遇上写得烂的我就会毫不客气地大骂"什么狗屁玩意儿,别糟蹋网费了!".我就这样狂热地点击,注册,回复,一直搞到连我自己都相信这样做很有意义为止。我差不多已把自己搞的神智不清了,有一次甚至冲我自己刚发的帖子回道:"去死吧!这种东西也写得出来,你也太失败了吧!"有时候坐我旁边的某个留飞机头的家伙会偷偷浏览黄色网站。说真的,我实在搞不懂怎么会有人对那种变态的东西感兴趣;我敢打赌任何一个稍有点审美观的人在第一次进黄色网站后就会对它们彻底丧失信心。那个傻小子是个十足的伪哩吧唧的家伙,他故意把窗口调到很小,好让别人以为那只是些飞来飞去烦人的广告——其实鬼才有功夫关心他在看的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呢!我能发现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一不留神点了不知哪个狗屁联接而使那些垃圾窗口成千上万地狂跳出来!我看着他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我拼命使自己不至于笑出声,可我的手却抖个不停,弄得鼠标也跟着哒哒作响,听起来倒很像笑声——这令那个可怜的家伙窘得简直要自杀了! 我玩五子棋的时候总会碰上一些男扮女装无聊透顶又骚得要命的家伙。他们在总快要输棋的时候求我悔棋,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会不断的发请求,更过分的是他们会用不知什么鬼程序发一连串诸如“让人家一次嘛”或“重来一次好不好嘛”等等嗲得要命的肉麻句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起差不多整张棋盘那么大一片鸡皮疙瘩。 我常跟人谈起我是多么地热衷于上网,可我暗地里觉得网上的东西总有十分之九是垃圾。尤其要命的是我总忍不住要把极有限的余钱耗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与我同寝室的老朱把我崇拜的跟什么似的,就因为我总能在网上随便骗到一打的美眉的电话,而且首先拾起话筒拨号的往往还不是我。他老是用一种透着鄙视的讨好语气向我套他妈的什么泡妞秘诀,可我能有什么狗屁秘诀!我只不过是在认认真真地敷衍她们而已,有时明明是她们愿意让我泡,却总装出一副无辜而又纯情的样子,让我想一想就忍不住要作呕。我真不理解竟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世界上存在“网恋”这么一回事,鬼才知道她们告诉你自己只有十八岁时是不是腰围已经超过了胸围,因为我就认识那么几个喜欢以女性身份在OICQ上大摇大摆招熊引狼的家伙,所以我就很能理解这个世界上会存在那么些个想变年轻的发情期老处女。 我差不多都快要忘掉我还是一个大一学生,我也许已经搞不清教学楼大门是朝哪个方向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是花在床上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发疯似的渴望自己大病一场,因为那样你就甚至可以连卫生间也不用去。剩下的小部分时间我会打打篮球,然后坐下来静静听上一段神秘园或小桥流水的CD,要是心情好,我或许还会听听H.O.T或斯琴格日乐。我不太喜欢H.O.T那五个人妖的样子,但我也奇怪他们竟拥有与自己外形极不相称的那种神奇嗓音。斯琴格日乐倒还不错,我觉得她的声音中有股薄荷味,我喜欢她用那高亢婉转的蒙古腔喊一些简单清爽的歌,至少那听起来让人感到怪舒服的。我挺讨厌那些唱歌的时候皱着假眉毛边摇头晃脑的歌手,也许本来皱眉毛或摇头晃脑并不是很难看,可关键是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嘴里还哼着一些比台湾剧还鼻涕邋遢的词曲,让我们欣赏起来总觉得是在嚼一块压根儿没味儿的香口胶。 我不知道自己这学期会有几门功课挂掉——我们私下里喜欢管某一门不及格叫“挂掉”——我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摸一下课本了。不过我可不愿去想象家里人捧着我的成绩单发愁的样子,我宁可不让这种事发生。于是,我不得不在考试前的几周突击一下了。 学校附近有一家不错的豆浆店,那个地方好就好在你只需要点一大杯冰豆浆就可以动也不动地坐上一个通宵。我当然指的是学习,而不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看那些无聊的汽车跑来跑去。实事求是的说店里的小姐长的并不是很好看,也许这并不重要,但我总固执地认为找好看一点的招待是餐厅对顾客的一种尊敬。当然这对小店来说只是道附加题,做不出来也没关系。 可实际上她们都是挺不错的女孩子,我指的是性格方面。有时你看她们陶醉在一些三流港台歌曲里的样子会感到说不出的难过,可她们总能自得其乐,虽然她们总是谦和矜持地为我端来一杯冰豆浆或其他什么吃的东西,然后坐在一边用羡慕的眼光看我捧着书本拼命装出苦读的样子,可我就是知道她们要比我快乐得多。 餐厅墙上挂着一个灭蝇器,时不时会有某只倒霉的飞虫撞上里面的高压电网,发出“啪”的一声响,像是为了礼赞这种献身壮举而放的鞭炮。可那些苍蝇或者蚊子什么的为何要不顾一切的飞进去呢,我实在是搞不懂。或许里面有某种值得它们送命的东西,又或许里面什么都没有,它们只不过是模糊了目标,在一片迷失方向的茫然里被冥冥之中的无形神力拉近死亡。 我猛得跳起来,想去看看那些苍蝇是不是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了。可它们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看不出痛苦和悲伤。我突然感到一股寒意逼上脊梁…… “我会变苍蝇吗?”回学校的路上,我发疯般地不住问自己。我觉得一阵恶心,于是朝地上狠命啐了一口,虽然我以前是从不随地吐痰的。 |
| 浏览:1018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