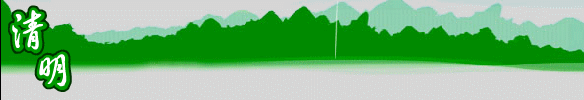回忆我的母亲(二)
小立
|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最困难的那几年就过去了,期间村子里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因为疾病和饥饿而死去,小姨却异常健康地生存下来,快速的长大,终于不再需要别人额外的照料,母亲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姥姥看她灵秀,做事也麻利,就把她送进几个村子联办的小学,指望她读些书,出来后能够进到镇上的纺织厂做工人,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可以吃上“国家粮”。于是,洗完了头,扎好小辫,换上新的蓝棉布褂子,挎上黄土布书包,弹落衲底花布鞋的灰尘,我的母亲终于走出了藤编摇篮旁和四角天井下的世界,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 刚一入学,母亲的聪明便如打开麻袋倒粮食一般显现出来,从第一次的期末测验开始,便包揽了几乎所有大小考试的第二名,之所以是第二名,因为同班中还有一个更加聪明的小男孩,一个来自隔壁村的坦克兵的儿子。那个时候每个班都有一男一女两个班长,自然由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人担任,在母亲的回忆中,她的这位搭档是个见多识广古灵精怪的家伙,也是班里唯一穿着胶底解放鞋和卡其布裤子的人,他背着货真价实的军用书包,虽然相对他来说有点大,他的家里挂着一张他和自己的兵爸爸站在真正的坦克旁边的黑白照片,中午带饭用的竟然是真正的炮弹壳做成的饭盒,这一切让他在班里的同学中间有了神一般的地位,成为一众泥小子拥戴的领袖,和小姑娘们暗暗关注的对象。 男班长就坐在母亲的后桌,有一双白净的手,削铅笔的技术却差到极点,总要拜托母亲帮忙给削。他因为聪明到不用认真听讲都可以拿满分,上课便常以拔坐在前面的母亲的头发为乐。那时的学校不存在素质教育这种时髦东西,这种举动往往招来老师拿细竹子做的教鞭一通猛敲,然后还要连累母亲跟他一起罚站,这对当时的小姑娘来说可是很丢人的事情。母亲羞愤难当,决定以不给他削铅笔作为报复,并不再理他,隔天却见他拿了上海冠生园的大白兔奶糖在母亲面前晃,剥开来往嘴里放,薄薄的糯米纸如玻璃般透明,一口嚼下去甜甜的奶香熏的人要醉倒,一嚼两嚼,母亲也就屈服了。于是,在某个春日的历史课后,被糖衣炮弹俘虏的母亲同男班长口头签订了丧权辱村的《下王埠条约》,在大白兔奶糖的诱惑下沦为了为阶级敌人削铅笔的帮凶。 那个时候样板戏渐渐兴起并已传到乡村的学校,喜欢唱歌、身体条件不错而且长相清秀的母亲最先被选进了学校的剧团,略加训练,她便可以轻易将腿拿到头顶。在几个村子里串演《白毛女》,母亲扮喜儿,开始的时候怯场,台上唱了几句就忘词,紧张的哭,台下的老乡还以为演的是改良版,大声鼓掌,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好了,该唱就唱,该跳便跳,该哭时哭,演到动人之处,自己哭得情真意切,肝肠寸断,台下的老乡受不了,眼泪也就跟着下来了。从此哭戏成了母亲的杀手锏,台上哀声一响,底下眼泪万两,姥姥本来不大愿意母亲参加剧团抛投露面的,看了一场之后便不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母亲要用功读书,不要放野了心。 有一年镇上出了一个大学生,在小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消息传到母亲的小学,男班长便偷偷告诉母亲,他有一天也会去上大学。母亲不太清楚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只隐约觉得那一定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距离她异常遥远的所在,那时的她,一直认为自己最好的出路便是能读完高中或中专,可以做一名教师或者像大姨那样进市区的工厂做一名工人。可惜的是,家境的窘迫无力将她的理想支撑下去,六年级刚上到一半,姥姥就让她退学了,从此,安静得课堂,舞台上的喜儿,不会削铅笔的男班长,通过读书而离开小山村的梦想,统统离母亲远去,母亲的生活,也再次回归平淡,那短暂的精彩,从此只能留在她的回忆之中,泛出些许感伤与遗憾。 |
| 浏览:574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