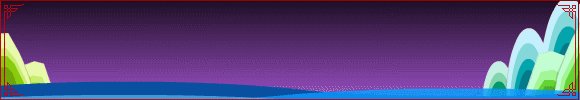沈从文只值一分钱 群星闪耀西南联大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
|
本专题撰文 叶成云(署名除外) 2007年06月12日08:31来源:《广州日报》 《上学记》何兆武(口述) 文靖(撰写)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历史,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师:胡适、钱钟书、陈寅恪、钱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吴宓、梅贻琦、华罗庚、冯友兰、金岳霖、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陈省身、吴晗……那些指点江山的同学:杨振宁、殷海光、汪曾祺、黄昆、王浩…… 活在老先生记忆中的西南联大,包含了他们的理想、才华与激情四射,当然还有邋遢、白眼和放浪形骸。西南联大自此成为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现代中国刻下无法磨灭的痕迹,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沈从文那教授只值一分钱”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刘文典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子把蒋介石给惹恼了。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梅贻琦安步当车 吴晗惊惶失措 大凡在危急在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有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杨振宁:“爱因斯坦老糊涂了吧” 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十八九岁的年龄,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 有一次,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茶馆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高干子弟在学校并不张扬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清朝大学士孙毓汶,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摘自《上学记》) 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每个周末,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北平图书馆借书,一借就是五本……一路上都是柏油马路,只有快到图书馆的一段路是沙路,自行车胎碾压在沙上的声音至今想来都是那么悦耳……” 多么惬意的读书时光!何兆武先生在这本口述历史小书中说,自己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可以一堂课几千年,也可以一年讲不完一个时代,一个话题。在先生看来,学术的生命力,正就在于它的自由——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何先生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读书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 这些美好的印象深深镌刻在何兆武脑海,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先生对于一次尴尬的借书仍“耿耿于怀”:“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我那时都五十多岁了,有次管理员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茶馆里听吹牛,里根挂二牌,这样的往事不仅让口述者颔首微笑,更让后来者心荡神驰。读这样的一本书,是一段幸福的旅程。 何先生反复地提到“幸福”。然而实际上,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在《上学记》、在学术随笔著作《历史理性的重建》、《苇草集》当中,何兆武先生都难以忘怀年轻时与好友、“大才子”王浩的那段关于幸福的争论。他用自己一生的沧桑经历,阐述了什么是“幸福”——“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的”。 诚哉斯言! |
| 浏览:888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民族脊梁
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