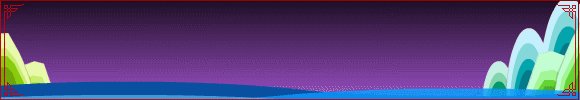沉入历史的湖
马风
|
百花文艺出版社马风 1992年8月24日,这是在北京举办的为期五天的首届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的最后一天。近百位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在这一天结束了围绕老舍的话题。而26年前这一天深夜,老舍在太平湖结束了他的生命。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太平湖早被填平了,已经没了踪影。但我还是要去看看。 我见到的是水泥围墙,高耸的厂房,空旷的场地,密密麻麻的铁轨。如今这里已经成了北京地铁国辆段的停车场。在晕黄的夕阳烘照下,这些由砖石混凝土钢铁构成的情景,显得格外暗淡单调沉重,没有一点和波光荡漾的湖水相关的痕迹。湖水,荷花,芦苇,野草,小径,连同老舍悲怆投入的身影和那伤痕累累的躯体,都已经荡然无存。这一切,像是沿着另一条“铁轨”,风驰电掣却又悄无声息地驶进了历史的“停车场”。 我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间。当年这个时刻,老舍在湖边一条长条木板椅子上,已经坐了十来个小时。他拄着拐杖,穿着千层底布鞋,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正像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将猎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住室内打开煤气开关一样,是下定决心要终结他的人生之旅的。可是,为什么在椅子上一直坐了十来个小时,此后又坐了将近六个小时,才迟迟地诀别人世呢。是心头闪着的那一点求生之火的余辉,还没燃烧殆尽?还是暗自选定好了的那个最后时刻,还没到来?但我猜想,他那被绝望的灰色泥沙淹没了的心田,许多人生情景仍然像未息的波涛,在挣扎般的翻腾,激起一圈圈难以静止的涟漪。如同把一本用生命写就的大书,读到最后一页,本该合上了,但却又情不自禁的要再重温一下前面的一些章节,进行一次盘点式的玩味,思索,反省。 老舍会想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那座小院。结束了在美国的漂泊生涯,回到了改天换地的新北京,就像他亲手在小院里种下的两棵柿子树,他的生命之树也扎根在这点个小院里,如今已枝叶繁茂有了16道年轮。这里有他的夫人儿孙用亲情用笑声为他酿造的天伦之乐。有上百盆一到秋天就争芳斗艳芬芳四溢的菊花。有他的书房,并不大,却是他勤奋笔耕的万亩良田,有过金色的丰收。书柜里一摞摞手稿,就是用心血记载着的耕耘底账。书桌上有齐白石为他精心镌刻的印章,还摆着他收藏的那位写过《闲情偶寄》的清代李渔用过的砚台。这座小院,因为幸福欢乐,即使结着蛛网的角落,也充塞着美满惬意。因为成功和荣誉,青砖灰瓦都一片辉煌。小院围成的家,多像一叶轻舟,载着欢声笑语,飘着诗韵茶香,荡漾在春花秋月中。然而,突然刮起风暴,使它帆折桨断,面临被险涛浊浪吞没的厄运。他知道,这里住着个叫老舍的人,所以才引来滔天大祸。坐在太平湖边的老舍,把脸朝向小院那个方向。看守公园大门的老人,向老舍喊着,时辰不早啰,该回家吃饭了您哪。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餐桌旁空着他的位置。这个位置永远要空着了。他仰天一声长叹,空空的肚肠里,涌进了满满的离愁别恨。 老舍会从丰富胡同19号,想到北京饭店。1949年年末,刚从美国返回故土时,夫人和儿女还在重庆。他这个远道归来的游子当做贵宾住在其中一间客房里。饭店与天安门毗邻,出来进去的,总可以看见广场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可以听见“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他很像杜甫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漫卷诗书喜欲狂”了。而这一年,老舍51岁,并不年轻,但仍然有一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勃勃朝气。在1950年全国文联的新年联欢会上,他踏上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才二十来天,就演唱了自己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他住的那间客房没有写字桌,他是伏在一张猜小的梳妆台上,写就了他的创作历史进入新中国阶段的开篇之作。 随后还是伏在梳妆台上连续写了《别迷信》《生产就业》《中苏同盟》等等作品。这样一些从篇名上就可看出属于应时文字的相声单弦,很难与一位曾经写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许多长篇名著的大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是对刚刚有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头衔的老舍来说,“为工农兵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那么崇高,又那么新鲜。真像看了《白毛女》抹着眼泪光荣参军的新兵,握着才发到手的那杆枪,急着想把子弹发射出去,好显示一个战士的忠诚和勇敢。老舍不能不写。而且,像这样以宣传配合时政为创作出发点,歌颂新北京新时代,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成了他后来一系列作品的高亢基调。老舍曾经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表示,“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正因为他“歌德”的业绩显著,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在群星灿烂的众多作家艺术家中,老舍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在他那慈眉善目淳淳谦和的脸上,总是难以掩盖住独占鳌头的新时代“状元”带来的欣喜和自豪。 入夜的太平湖,不见几点灯火,被无边的暗淡和凄迷所笼罩。坐在湖边的这位“人民艺术家”,心际间更是没有一丝亮色。他一点也没有了“状元”的感觉,倒是有一团化解不开的困惑,沉甸甸压在他即将终结的思绪里。他这个忠心耿耿的“歌德派”,怎么会一夜间变成“牛鬼蛇神”了呢?眼前微波晃动的湖水,忽然成了一片烈焰跳动的火海。就是昨天,在成贤街孔庙大殿前,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红卫兵”,上演了一出狂热的闹剧,更是一出惨烈的悲剧。戏曲舞台上包文正的蟒袍玉带,杨玉环的凤冠霞珮,窦娥的一袭素衫,诸葛亮的八褂仙衣,一件件绣制精美,针线间闪耀着中国传统文化绚烂色彩的戏装,作为“四旧”的罪证,像抛弃垃圾一样,统统投入火中,化为一缕缕灰烬。就在这堆焚烧着历史焚烧着文明焚烧着艺术的火堆旁,由老舍领衔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脖子上挂着“黑帮”牌子,被一双双紧握皮带的手,压住脑袋跪成一排。 刹那间,在他精神天地里挺立着的那根支柱,遭到了巨斧的砍伐,轰然倒塌下去。突然变得一片空白的头脑,闪现出他在《茶馆》里为常四爷写的一段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这句看似平常的发问,由首都剧场舞台上那位常四爷的扮演者郑榕说出口的时候,老舍总是浑身一阵颤栗,鼻子跟着也酸了。他自信这是为这个人物写得最好的一句台词,算得上得意之笔。此时,跪在孔庙前的老舍,猛然醒悟到,这句台词原来也是写给自己。 夜渐渐深了。湖中闪出的黑色波纹,飘出丝丝寒意。已经尝尽人间冷暖也写尽人间冷暖的老舍,还是只穿件衬衫,雕像一般地坐在木椅上。身边的灰色中山装,依旧那么放着。远处的喧嚣也被浓重的夜色驱赶走了,只有李铁梅还在一支高音喇叭里“高举红灯闪闪亮”。隐隐约约传来的豪迈誓言,倒是胜过了寒意,触动了老舍。他又一次想到舞台,想到北京人艺的排练场,想到于是之郑榕朱琳蓝天野这么一些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们一点也不比他曾在百老汇舞台上看到的那些著名演员逊色。遗憾的是,给他们写的能够尽情展示表演才华的好戏,太少了,实在太少了。也就是《茶馆》《龙须沟》这么两三出吧。他心里有数,这16年,总共写了23部剧本。仅其中的《春华秋实》前后就重写过10次,累计有五十多万字。那么,为这23部剧本,他在稿纸方格里,究竟填写进去多少个字呢?真是很难统计了。而且,填写进去的仅仅是一个个方块字吗? 不,他还填进了16年的赤胆忠心,16年的废寝忘食,16年的流金岁月。对如此巨大的付出,老舍很长时间都当成一种荣耀,无怨无悔。但是,一个大作家的艺术良知,仿佛不停响着的晨钟暮鼓,到底敲响了那颗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头脑,使他回复了冷静。他不想承认,又不能不承认,16年的创作收获,夹杂着不少折扣,与付出的巨大代价,并不成比例。这16年来,他放弃了那么些生活积累,那么些艺术构思,那么些名著的胚胎。最终放弃掉的,是一个杰出作家无比珍贵的写作生命。 就在四个月前,老舍顶着北京的风沙,到香山看望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女作家王莹。她住的地方叫狼见沟,挺吓人的名字,可见多么偏远荒凉。这也看得出,这位女作家回国之后,距离文学界主流还是很遥远。此时,位居北京副市长高位的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正遭受批判。在这么个时候,老舍从城里跑到山沟,来看这么个作家,可以说对他的人大代表,文联主席,“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是个不小的背离,他正像一个普通作家的位置回归。而且,他这次私人性的拜访,是他告别人生之前最后一次社交亮相。在王莹那间深藏在荒山野林,远离喧闹远离是非的小屋里,老舍找到了一处可以是紧绷绷地神经放松一下的清闲之地。这样的机会,以前太少了。以后呢,怕是没有了。所以在安慰鼓励过王莹之后,老舍吐露了肺腑之言。他说“公事多会议多应酬多”,“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 老舍终于从木椅上站起来,在人生大限的门槛上徘徊了十几个小时,他带着68年的世间风尘,一步一步地向黑幽幽的湖面走去,向另一个世界走去。他没拄手杖,像是没了腿疾,穿着前层底布鞋的两脚,迈动得格外平稳从容。他眼里的湖水,就是上天洒下的甘泉,什么功名利禄摧残凌辱悔恨绝望,都将在这里洗刷一空,化为缥缈的烟云。北京有不少北海昆明湖积水潭这样的名泊大湖,老舍却选择了鲜为人知的太平湖作为归宿。他相中了这里的寂静,这里的平常。老舍或许没想到,他的身影消逝在水纹中之后,寂静的湖面上,立刻爆响了惊天的霹雳,全北京全国全球都受到了剧烈的震荡。而平常的湖水,也因为他身躯和声名的沉入,变得丰盈和厚重,从此与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浩浩荡荡的融汇在一起了。尽管十几年后,这里被改革开放的蓝图带来的水泥砂石沥青沉大海夷为平地,但潋滟的湖水仍旧在历史深处波光闪闪,波光闪闪。 |
| 浏览:1064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民族脊梁
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