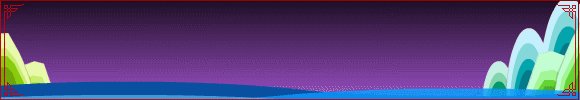峥嵘岁月5
邰杰(此篇较长)
|
九、我的朝鲜阿妈尼
在全世界许多种类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有着非常相近的读音,那就是“妈”这个词。我不懂为什么,是因为“妈”这个音节容易发出,还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妈妈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母爱呢?我想大概两个因素都存在。是的,我不仅享受过生身母亲的爱和抚育,也感受过朝鲜阿妈尼的挚爱和关怀。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一位普通的朝鲜阿妈尼的形象常萦绕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1951年冬季,我工作的单位志愿军第三野战医院驻扎在朝鲜遂安邵边济里小村。说是村子,实际上大部分民房已被美帝国主义飞机炸成废墟,仅在山脚下尚留有数间弹痕累累的茅舍。住在这残存茅舍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因为防空洞的潮湿和阴冷年轻人都受不住,更何况老人!我们医院到这里后在山头上建了许多防空洞,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均住在山上防空洞里。医院院部的防空洞离村子较近,因此,院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吃饭时常借用阿妈尼家的房子作临时饭厅。当我们第一次脱掉鞋子走进阿妈尼家炕上坐下吃饭时,发现小炕桌上有一只大铜碗盛着带些锅巴的热水,还有一碗北瓜炖土豆。这菜和水是哪儿来的?政委忙问翻译员小金,小金说这是房东阿妈尼端上来的。接着,我们就看到一位五十多岁,满脸沧桑,身穿白衣白裙头扎白毛巾的朝鲜阿妈尼从厨房走进来。她面带笑容,表情里饱含着对志愿军的敬意,说了许多话,只是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小金给我们翻译说:“阿妈尼说,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好,帮助朝鲜人民打美国鬼子,把美国鬼子和李承晚兵赶到‘38’线以南,我们老俩口才敢从山上防空洞里搬到房子里住。志愿军战士从老远的中国来到我的家,但现在打仗很困难,我没有别的食物招待,只有自己种的一点北瓜和土豆,对志愿军同志表示一点心意。”说完,阿妈尼就微笑着退回厨房去了。我们吃着这北瓜炖土豆,喝着有些糊味的热水,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吃到了妈妈亲手给我们做的美味食品。但我们志愿军有纪律,饭后,政委让翻译小金给阿妈尼送去朝币,作了解释。阿妈尼一脸疑云,很不理解,小金再三说服,这才作罢。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对阿妈尼的家庭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的老伴在美机一次轰炸中受了重伤,至今行走不便,不能干活。她两个儿子都参加人民军上前线杀敌去了。因此家里家外的活都由阿妈尼独自承担,种地、收割、顶水、打柴、抢修公路、支援前线。她整天忙碌着,一副坚毅不屈的神情,似乎天塌下来她一个人也能顶着。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年轻男子几乎都参军上了战场,但千千万万的朝鲜阿妈尼和全体妇女大军,用头顶,用坚强意志、以伟大母爱支援着人民军和志愿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记得有一次,我的胃病犯了,呆在阴冷的防空洞里,吃不了饭,连喝水也疼,疼痛使我手捂胃部、缩成一团。正当我蜷缩在防空洞一角痛苦难耐之时,防空洞口闪进一个穿白衣白裙的人,阿妈尼来到了我的身边。细心的朝鲜妈妈发现我有好几顿没有到她家房子里用餐,就来看我了。翻译不在,她不会讲汉语,我只会叫“阿妈尼”。但通过手势、表情,我们俩居然沟通了。我明白了阿妈尼的诚意,是让我到她的房子里去休息。拗她不过,我就随阿妈尼到了她家,她给我安排在炕头最暖和的地方躺下,并给我盖上了她家仅有的一床棉被。接着,她又到厨房,不一会儿给我端上一碗热汤,示意我趁热喝下去。热炕、热汤,还有阿妈尼那颗热心及一双温暖的手,暖热了我的心,减轻了我病痛之苦。我想起了已去世三年多的母亲,回忆起我幼年时有点小病小灾妈妈为我做的薄面片汤以及妈妈的疼爱。噢!阿妈尼,我的朝鲜妈妈!您真像我的亲生妈妈!我心底呼唤着妈妈,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在阿妈尼悉心照料下,我的胃病很快就养好了,阿妈尼脸上的阴云也消散了。可没过多久,部队医院向前方移动,我们跟阿妈尼依依惜别。这位在战争中坚毅不屈的母亲竟老泪纵横,拉着志愿军同志们的双手不愿放开,送了一程又一程。 阿妈尼,朝鲜妈妈!您老人家如果今天健在的话,该有一百多岁了,我衷心祝福您。如果不幸您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永远怀念您。 注:“阿妈尼”朝语,即汉语“妈妈”。 十、回忆我的第一个上级 1999年元旦,我收到一张贺卡,贺卡上仅写有一首小诗,题名《思》,诗文为:“我住沈阳你长春,多年不见思念君;有朝一日重相会,说说笑笑论古今。”这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现在统称为老战友者候心—老人写来的。耄耄之年的老者,用他曾被日本鬼子两发子弹穿透过的右手,颤抖地写下这首深情的思念老战友老部下的诗名。阅后我百感交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往事如流水一样倾泻而出。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10月,我刚脱掉学生装,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满怀热情、踌躇满志,开始了革命军人生涯。我们这几百名学生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文化干部训练队接受几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后,就被分配到全军各有关单位。女兵分配到文工团的最多,也有到机关做文化干事或到师部、团部当文化教员的。那时分配工作是单向选择,个人服从组织,那里需要就在那里干,不会干就从头学起。 正式分配前,有一个高个子约30多岁的军人找我个别谈话,他脸上布满浅浅的麻子,眼睛不大,外表看起来有些严峻。他跟我谈话时我不敢正视他,有些胆怯。他问了我的文化程度和爱好,我说参军前是高中学生,挺喜欢文学的。他问我:“军政治部文工团需要人,你同意去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服从革命需要!”但我心里却打起了鼓,心想:我唱歌变调,舞蹈也没有基础,乐器又从没摸过,到文工团我能干什么呢?但革命工作是不许讲价钱的,我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跟大个子军人到了四十军文工团,心想见了文工团的领导再讲困难吧。到了文工团才知道,原来找我谈话领我到文工团的那个大个子军人,就是我们军政治部的新任团长侯心一同志,我想谈困难提条件的事压根儿不敢提了,于是,侯心一团长就成了我的第一个上级。 在文工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对侯团长的革命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在与日本鬼子拼杀时,右手被日本鬼子的枪弹穿了两个洞,至今右手内还有三小块弹皮未取出,成了三等残废。他由普通—兵逐步成长为部队文艺骨干,文艺团体领导。侯团长能编能演也能唱,他编写过独幕及多幕剧,也写过小调剧和快板书。他参加过几十部歌剧,话剧的演出。在话剧《抓壮丁》中,他饰演王保长一角,把王保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形象塑造得维妙维肖。有一次演出,当王保长被愤怒的群众打倒在地,侯团长顺势躺下装死时,他的刚两岁的小儿子在台下竟被吓得嚎啕大哭。团长夫人也是文工团员,有时演出不得不把孩子带到现场。侯团长的音乐素养也不错,识简谱,能创作歌曲。我对音调、音符、节拍等音乐初步常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的确,侯心一团长既是我们文工团的好领导,又是我们年轻文工团员的严师。早晨他领我们练声,我最怕单个教练,唱不准音调,他会猛剋我。他教我们识简谱,记五线谱,教我表演基本功,还指导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平时,他待我们文工团员像父辈,像兄长,温和而平易。他对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团员称呼也特别,总爱加个“老”字,常是“老曹”、“老王”、“老邰”地叫我们。实际上曹华和王学艺当时只有16岁,而我也不过18岁。 1950年1月,我们四十军第一批抗美援朝赴朝参战。在遴选女文工团员赴朝参战人选时,八名女将中竟有我的芳名,那兴奋、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好几个不眠之夜都在想着如何在抗美援朝前线经受战争考验,如何为人民立功。那种光荣感、自豪感不用说了,只觉得文工团侯团长为首的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产生“士为知已者死”的感慨,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会义无反顾。 在朝鲜前线极其限苦危险的条件下,我还坚持写了部分战地日记,日记除写敌机的狂轰滥炸,战争残酷之外,也反映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有一篇日记抱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地主家庭,这对自己的进步有多么不利啊。有一天,侯团长看到我时问道:“老邰,到朝鲜前线后有什么感想呀?”我回答说:“我记了日记,请团长看一看,算是我的思想汇报,也希望您给我改正错别字和病句。”侯团长说:“这可是你主动送给我看的,我就看看吧。”当我拿回日记本时,字里行间有红铅笔圈出的错别字,还发现有几篇日记旁边有眉批。侯团长针对我夜行军后的表现批注道:“似这样的疲劳现象,如何经得起更严酷的考验呢!”。在我抱怨自己的出身会影响我的进步时,他批注道:“一个人的出身成份对他的进步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如何而定。”是啊,侯团长在鼓励我,也是在鞭策我努力进步。其他许多团员的日记本上也有团长有针对性的批语。 文工团领导根据我的所长分配我搞创作编写文艺节目,我根据搜集到的英雄事迹材料和另一位团员合编了《歌唱青年英雄曾南生》的大鼓词,演出后效果颇佳,为此,团长为我请了功。 由于战争条件的艰苦,我竟病了,得的是一种由人虱传染的急病“回归热”,高烧不退。文工团里的女卫生员照顾我在一个防空洞里休息。侯团长知道后来看望我,他像哄孩子似的对我说:“老邰呀,你想吃点什么?我这里还有一听肉罐头,你吃下去病就能好啦!”我含泪接了,但却无力打开,团长又亲手为我打开罐头,看着我吃下去方离开。晚上夜行军时,侯团长看我发烧走不动路,就将配备给他骑的一匹军马让给我骑。侯团长吃力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骑在马背上禁不住流下热泪、唏嘘不止。 后来,我和侯团长先后调离文工团,1953年部队回国后,侯团长调到军文化处任处长,我于1954年考入大学深造,也转业了。自此数十年间音讯杳然。几十年来,在我内心深处,对我的第一个上级,对我人生旅途上最好的导游者始终心怀感激和尊敬。经过我的多方努力和无数次探访寻觅,终于找到了老首长的通讯地址。从1996年我们通过书信联系了几次,我本打算到沈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因我家事烦忧,老公先是生病住院,接着是不治而逝世,我心绪不佳终未能成行。1999年接到老上级的贺卡,当时我在北京住,心想2000年夏天一定到沈阳去跟老团长“说说笑笑论古今”。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让我遗憾终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敬爱的老领导,第一个上级、我的严师、犹如父辈和兄长的侯心一老人竟于1999年10月作古仙逝。呜呼!“有朝一日重相会,说说笑笑论古今”竟成了他未实现的遗愿,那张贺卡也成了我的第一个上级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墨。 谨以此文作为对我的第一个上级侯心一革命前辈的祭奠和悼念! 作者简介:邰杰, 女,1932年1月出生,河南南阳人。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不久分配到四十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1950年冬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军抗美援朝赴朝参战。1951年6月调到志愿军第三兵站医院任文化教员。1953年10月朝鲜停战后回国。1954年9月-1956年8月在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调干学习。1956年9月毕业分配到长春大学(前身:长春计划经济学校、长春机械工业学校等)工作,任语文教师。1985年晋升为中文副教授。1988年退休。以上文章系作者亲身经历和感受。 地址:130025 长春市南岭大街15号15-10门209室 电话:0431(8669023) Email: weihongz@public.cc.jl.cn Xucy@norfico.com.cn |
| 浏览:954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