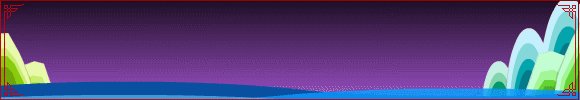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出版前言
萨都剌
|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出版前言
晚唐五代以还,讫于终宋之世,广袤神州,政权割据。四百余年,金戈铁马,攻伐不已。或有间歇,杀机仍隐伏于一时相安之中。元蒙起自漠北,虎视中原。初则干戈染血,专事屠戮。至于忽必烈,遵儒学,行汉法,攻城略地,兼以道义征服人心,终成天下混一之业。 元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其历史背景,阶层构成,文化传承,有别于历代封建王朝。故其观念形态,政策方针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心理,兼容意识。华域内外的社会剧烈震荡,把汉族以外的诸多民族的知识分子卷入时代巨大变革之中。在一定政策保护下,全社会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的失落,民族自我价值的重估与肯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终以华夏土地的当然的主人之一,从容地跻身于政路文坛,并成为发展,开拓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新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其态势,其成就,可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黯然失色。在文学领域中,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他们的巨大创造力和突出成就,更堪称史无前例。回回民族生成于兹,回族文学起步于兹,萨都剌当是这个时代文坛巨子,更是古代回族文学杰出代表。 萨都剌因自祖父始,以世勋镇守云代,定居于雁门(今山西省代县),故自称雁门人。元代至正年间其手定个人诗集题名亦作《雁门集》。是集为八卷本,已佚,今仅存其友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干文传序。 萨都剌诗为后世所重,故明清以来屡有刻本。明成化乙巳(1485)兖州太守赵兰得沈文进家藏旧本并锓梓于郡斋是为最早之再刻本之一。复有明弘治癸亥(1503)李举刻本题曰《萨天锡诗集》为五卷本。明万历潘是仁校刊本《萨天锡诗集》为八卷本。明末有毛晋汲古阁《元人十种诗》本,则为三卷,集外诗一卷。此外,尚有包山叶石君校本等。 萨氏后裔亦屡为辑刻。初刻于明天顺己卯(1459),再刻于康熙庚辰(1680),皆为六卷本亦题《雁门集》。清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萨龙光本(十四卷),广泛搜罗当时所见诸种版本互相参校,故较为完备。据萨本今人殷伦与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最为常见。因未能参校他本,更无辑佚,仍留下诸多遗憾。 萨都剌诗刻本虽多,但因元末战乱,散佚更甚。据萨龙光《雁门集跋》云:『公《南台月》诗云「黄河太华三登临」。是公尝到华州,而集中无一诗,此其佚也。他如张贞居《句曲外史集》有《答次韵见寄》七言绝句一首,李季和《五峰集》有《和字韵》五言律一首,《和秋日海棠韵》七言古一首,《次萨某韵》七言绝句一首,《次萨郎中次萧御史韵》七言绝句一首,《次韵杂咏》七言绝句四首之一、二、三首,今集中并失之矣。若夫《宫词》二十首见于杨廉夫和序,七言律《巧题一百首》见于干寿道本集序,《西湖十景词》一卷见于宣德《仁和县志》及邵远平《续宏简录》。凡皆前载之有可考,因得指其篇之亡也。而其余散佚所不及知者,又难以指数矣。』 此外,因传抄之误,审校不精,移萨诗于他人集中者亦多。如《次韵送虞伯生入蜀》误入马祖常《石田集》中。《山中怀友》六首,《题黄赞府斋中十咏》,均为黄溍《日损斋稿》误收。至于卢琦《圭斋集》岁久失传,后人搜而梓之,半数为萨氏之作。倘萨诗传本有失且又无从考据,当难于厘正。 今传日本民友社刊本《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印行不过五百部,国内亦为罕见,却是《雁门集》之外的重要版本。可惜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以下简称《逸诗》)刊行于明治乙巳年(1905)。其所据版本为日本北朝后圆融院天皇永和丙辰年刻本。永和丙辰,正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萨氏手订《雁门集》,干文传为之作序题为至正丁丑。据陈垣先生在《萨都剌疑年》中考辨,干序当作于至正七年丁亥(1347),则永和本《逸诗》上距萨氏亲自编订《雁门集》仅29年。萨都剌生年卒年众说纷纭。倘从萨龙光之说,萨都剌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乙未之后,即公元1355年之后,日刻本距公之辞世,仅为二十年左右。故《逸诗》应是流传至今萨氏诗最早刻本。仅此,《逸诗》之地位不可轻估。《逸诗》明治重刻本校勘者岛田翰先生称其亲见永和本『相其版貌,盖据元季刻本所覆镌。』但是,未知其出于何年刻本。因而《逸诗》之可靠性似亦不容置疑。 岛田翰为日本著名学者篁?岛田次子。其母亦出诗书名门,故自幼耳濡目染,学有本原。岛田性癖独爱古籍,尤喜校勘。后从师于井井居士竹添光鸿先生。井井居士爱其才器不凡,自信之笃,因材施教,不强其所难。除尽出自家所藏唐宋古籍,使其饱饫其中,复荐之于内府,得以博览中秘珍藏。校勘之学造诣日深,终成一代名家。俞樾盛赞其雠校之精,所见之富,以为『自来校勘家所莫能及』。这位清末大师曾被曾文正公许为『真读书人』,他敬服岛田先生,亲书『真读书人』四字为赠。表达了这位中国学者对岛田翰先生关心华夏文化,精心致力于汉文化发掘与整理的赞赏之情。 除早佚之至正二十卷《雁门集》外,其它刻本岛田翰均有考求。鲜为人知的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年间(1596--1614)所刻《萨天锡妙选稿》亦曾亲见,并在其中发现后人搀入《天满宫》诗一首。足见岛田翰校读之精细不苟。 其校勘原则是『必慎必遵』,鉴于后人多有一知半解、臆改古人著作之弊,故颇重旧刻原貌。甚而『虽知其显误亦不敢校改』。《逸诗》原貌基本保持,是其长处。是非,异同当校末校者亦多,是其缺憾。 《逸诗》收入七律138首,七绝3首,五绝1首,共142首。后附有僧释疏文7篇。据岛田翰查考,其中七律89首,七绝2首,五绝1首,皆《雁门集》无载者。《逸诗》中《登镇阳龙兴寺阁观铜铸观音》为七绝。《雁门集》中则为七律,似是《逸诗》截七律而误作七绝。 今据新刻《雁门集》详查,《逸诗》与之互见者七律53首,七绝1首。《雁门集》无载者七律85首,七绝2首,五绝1首。显见《逸诗》中88首,当是名符其实佚诗,弥足珍贵。其余互见者极多异同,可以相互补正。 至正本干文传序云。『有巧题百首,皆七言律,别为一集。』毛晋《集外诗跋》亦称『有巧题七言八句别为一集,余未曾见。』查《逸诗》七言律诗138首,其中,巧思巧笔而成的精巧咏物诗有62首。岛田翰认定前人所谓萨氏生前手定的皆七言律的巧题百首,正与《逸诗》相合。《逸诗》当是『明清之逸篇,而天锡在时已为《雁门集》以外之单行本也。』愚意以为巧题百首,别为一集,是萨都剌咏物诗集。为干文传所见,亡佚于其后。《逸诗》则为萨诗别一选本,只是保存了其咏物诗集《巧题百首》中之大部作品。另有部分巧题咏物之作,留存于萨诗其它刻本中,亦有搀入他人作品之中者。萨龙光辑刻十四卷《雁门集》中有《鹤骨笛》、《天灯》、《雪花曲》、《车中女》、《美人纱带》、《仙坛》、《虾助》、《手帕》、《雪米》等咏物七律即是。萨龙光在《鹤骨笛》、《天灯》二诗案语中云:『以上二诗,亦从毛本集外诗补收,即?毛本编次。《鹤骨笛》诗或属龙子高作,恐误,盖二诗与《手帕》、《雪米》、《虾助》、《车中女》、《美人纱带》当皆《巧题》百首中所遗者。』萨氏所说不差。 元人以咏物诗名于世者为金陵人谢宗可,其生卒不详。有集行世曰《咏物诗》。清人顾嗣立于《元诗选》中称:『宗可金陵人,有咏物诗百篇传于世。汪泽民题其卷。』汪泽民《谢宗可咏物诗叙》云:『本朝金陵谢宗可为咏物诗数百篇。』今查《咏物诗》集(乾隆辛亥年刊《冰丝馆藏板》)共得诗406首,皆为七言咏物律诗。其中有些与《逸诗》互见,值得推究。 《咏物诗》序,汪泽民作于元至正癸巳,即公元1353年。《雁门集》序,干文传作于至正丁亥,即公元1347年。可证《雁门集》及《巧题百首》早于《咏物诗》而成集。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金陵谢宗可有《百咏集》大率皆效萨诗。』可见萨都剌巧题之作,早于谢宗可,并为谢氏慕而仿作。因二人咏物诗体制风格一致,早已成集之《巧题》百首,难免因辗转传抄致使一些作品搀入《咏物诗》(亦作《百咏集》)中。《虾助》诗,咏水母(海蜇)之作。郎瑛《七修类稿》指出,《虾助》诗为萨天锡作,『萨诗予家所藏可谓全矣,亦失此律。』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也指出,《虾助》诗乃误入谢集中,实因后人不辨所致。鉴于上述情由,误入谢集中者,当非只《虾助》一诗。《逸诗》与《咏物诗》互见者,似多应归于萨都剌笔下,恐非掠美。 萨都剌生平仕履,不见于正史,似雾豹冥鸿,难窥全貌,极不分明。《逸诗》则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有助于理清某些大相径庭说法。 干文传与萨都剌相友善,其《雁门集序》所言萨氏种种应是基本可信。及第于丁卯(1327)已成定论。唯及第后即应奉翰林文字事,诸说不一。萨龙光认为及第后,是秋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十二月以事赴京。据欧阳玄《圭斋集》载,崇天门传胪赐进士,是在泰定四年丁卯八月十二日。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亦作八月。按萨龙光之说可见及第后未授应奉翰林文字,实时赴任镇江。而干文传序称,及第后即授应奉翰林文字。另一说认为同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次年泰定五年(1328)始授镇江录事。 《逸诗》中有《涧泉明府见示病中佳作次韵述怀》二首。内有『西邻隔屋送新酒,北固登楼入醉吟』之句,可知诗作于镇江。『负郭有田归更好,还家无日梦难凭』,写出了诗人身居末僚,倦于仕途,归心之切。此诗无疑作于京口任上。其中『郄忆玉京天似水,奎章楼阁晚沉沉。』足证萨氏任应奉翰林文字是在授职镇江录事之前。赴任镇江应在中举后次年为是。 关于萨都剌任职镇江录事年龄有57岁,29岁,21岁等几种说法,这又关系着萨氏生年卒年的推算。《逸诗》有《次依前韵六首》,其中有『去年曾见战旗舒』,『血染潼关百草枯』之句。萨氏所言潼关血战,系指泰定帝死,皇子阿剌吉八即帝位于上都,改元天顺,燕帖木儿于大都发动政变,迎武宗子图帖木尔为帝,改元天历,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并立,战于潼关一事。萨氏授镇江录事是天历元年(1328),此诗则是追记『去年』事,写于天历二年(1329)。诗中有『儒生白面秀眉舒』、『扬子江心照黑须』之句。在《病起登楼见民间火哀以赋之》有句云:『日来顿觉病怀舒,憔悴参军绿发须』。古人常以绿形容头发乌黑发亮,如晏几道《鹧鸪天》:『君貌不长红,我鬓无重绿。』吴均《和萧子显古意》:『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减』皆是。从上述诗句中『黑须』、『绿鬓』可以断定,任职镇江录事时的萨都剌正值少壮之年。故萨氏生于1300年左右之说,更为准确。 萨氏为人刚正,有矫世变俗之志。任侍御史于南台,竟以弹劾权贵左迁(邵远平《续宏简录》)。奉镇江录事职,敢于惩治为害一方的太守家豪奴(清光绪《丹徒县志》)。守正不阿,敢撄逆鳞的烈烈男子性(回族性格的具现)在《逸诗》中多有表现:『平生意气惯豪舒,肯拂人间宰相须』(《次依前韵六首》)在《寄文济王府教授郭尚之》诗中,藉用冯驩故事,『欲笑冯驩事干谒,无鱼弹铗向侯门。』同样表达了不媚权门,自尊自重的人格追求。 对于人民,他凭着赤子之心以教化为重,据《至顺镇江志》载,萨氏在录事司职所,亲书『?教』匾额以自警自励。如镇江『俗尚巫,以祸福惑愚民,都剌捕治之。』(《镇江府志》)对于百姓疾苦,同样极为关心。镇江灾荒,他建言太守发?以赈,全活数十万人。由于他有济世苏民之心,且多善政,故深受百姓爱戴,『吏民喜见参军面,水宿风餐鬓发焦。』(《过京口城南桥》)他的从政艰辛及吏民对他敬爱之情,读之令人动容。《逸诗》中《病起登楼见民间火哀以赋之》则写他亲见京口城内一次大火的痛苦心情。 戴良在《鹤年先生诗集序》中云,来自西北诸国的少数民族,奉职称藩以来『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巨大的历史变迁,冲击着固有的传统文化,改变着世代传承的生活模式。但是,对于文化积淀丰厚的民族成员来说,他们往往在心理深层对文化传统仍然有着难以消除的自认感和自恋情绪。来自中亚地区的色目人,他们被掳掠东来,终成为元蒙征服宋、金,完成统一大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故有习武风尚。萨都剌祖父萨拉布哈即以勋功留镇云、代。至于萨都剌虽已弃武学文,但是,尚武传统,效命疆场的向往并没有失落于青灯黄卷之中。这在《逸诗》同样有多处表现。他以仰慕之情写边功赫赫的沙场老将『郄喜汉庭诸老将,操戈矍铄尚贪功』,并激发了自己『愿学闻鶏舞剑雄』(《梅岭》)的奋进之心。虽是『儒生白面秀眉舒』,他郄怀抱慷慨,希望『铁甲勇提三尺剑』为国奔驱。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他仍是『五更豪气三千丈』,『五更飞梦入穹庐』(《次依前韵六首》)足见其投身戎马的执着。此外如『少壮金戈探虎穴』(《南安镇抚许南山奉表赴西省送别》)『倚剑试登楼上望(《到黄州》)无不表现着一个勇武民族难以消失的潜意识和独特的文化心理。 《逸诗》中的巧题62首。代表着元代咏物的新的成就。咏物诗已见于诗经,六朝更盛。唐代以来,渐渐成为中国诗歌中一个重要题材。咏物诗,在元代更是别开生面。据笔者所知,元人为诗者,大都有咏物之作。萨都剌、谢宗可更是擅于咏物,且独立成集者,清人乔亿《剑溪说诗》云:『咏物诗,齐、梁、唐初为一格,众唐为一格,老杜自为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宋诗粗而大,元诗细而小,当分别观之,以尽其变。』所谓『细小』,当是文笔细腻为其长,格局狭促为其短。元人咏物,未可尽称『细小』。萨、谢二人有些咏物诗流于『细小』确是事实。 萨都剌所咏之物有极微细者,如花雾、霜花、水纹。取材者小,自然不易超脱其上。一番轻钩细抹,难免纤细、琐碎。由于萨氏为大手笔,咏物诗同样有流丽清婉特色,无句锼字刻之艰涩。且笔带情韵行,物性与人情两合,既可赏玩于目,又可撩情于心。实有过于侪辈者多矣。如《佳人手》诗,如此题材,易入于轻佻、浮薄。萨氏郄通过佳人纤手的不同动作,多侧面地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百无聊赖的苦?和深切的内心痛苦。诗人不是旁观的浮浪子弟,而是以真情注入,直似抒写自家心事。结尾『几番欲绣回文字,惹起相思却住针。』细微的手势,精微的心势,在不易觉察的变化之中,却内蕴着巨大的情海波澜,足可动人情思。 有的咏物诗,只是一番描摹,表现个人独特感觉,如《晓色》一诗。晓色,本是司空见惯,诗人郄在习见中,特辟一境,给读者开出一个新的艺术欣赏空间:『远似烟霏近又空,非明非夜两朦胧。一天清露洗难尽,几抹曙云遮不穷。断角楼台浓淡里,残灯院落有无中。苍茫半逐鶏声散,又被朝阳染作红。』晓色,只是瞬间,诗人从远近高下多种视角,从声音,色彩多种感受,写出了晓色的极细微的特点和渐渐天光的变化。读来如见如闻,极生动,极逼真。 不离咏物,是咏物诗根脉。只是咏物,过于黏着,底蕴浅啬,不能超脱,则是咏物诗之大忌。《逸诗》中咏物诗,确有些藉物咏怀,又不离咏物诗本色的佳制。如《网巾》以『头上任渠笼络尽,有时怒发亦冲冠。』作结,一幅网巾,仿佛成了官场网络,人生羁绊,名缰利索,拘囿着自由脚步,紧束着美好人性。诗人愤怒着,最终要挣脱。寓意颇深,都在物性,物态的准确摹写之中。这种把生活的哲理浓缩于似乎与之了无关涉的事物之中,是以对生活感悟多,理解深为前提。物的触发使情思勃然。写物不凝滞于物,而是离形得似,似中求其思致高远,别有寄托。给予读者的是理性的满足,理性的升华。萨都剌笔下如此绝妙咏物诗非只一首,但仍嫌贫乏。 《逸诗》流传不广,尚无人对它进行研究考证。不揣固陋,只是对《逸诗》进行一些粗浅分析,以为抛砖引玉。 我作为国家科研项目《全元诗》副主编,几年的埋首元诗,对于传统的轻贱元诗,已是深深不以为然。清王士祯所说:『耳食纷纷说天宝,几人眼见宋元诗』,袁枚所说『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我深服膺王袁二公之睿智灼见,且又颇中下怀。《逸诗》的校点与刊梓,是应声古人于数百年之后。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元诗》第一卷问世之后,有更多知音投身于元诗的开发,去拓出一片片新绿。 回族古代文学研究方兴未艾,《逸诗》在国内刊行,对于萨都剌研究,回族文学的研究无疑会给予些微影响。作为一个挚爱自己民族的回回学人,我欣喜,我感赞。在此,不能不向山西古籍出版社及孙安邦同志表示感谢。 《逸诗》本应影印出版,以保持本书原貌。为了照顾一般读者,在力求不失原貌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校订。限于个人功力,难免疏漏,还望海内方家赐教。 李佩伦一九九○年斋月于北京安优轩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书影) (缺) |
| 浏览:586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25